英语六级考场外,静默的杭州上空开始飘起了雪。那雪就像江南连绵成线的冬雨,淅淅沥沥,如柳絮飘荡,又似漫天白练。
老人说,瑞雪兆丰年。那厚厚的白皑盖在不再生息的万物之上,宣告着庚子年的尾声。都说风起于青萍之末,可2020年这场疫情,让年初所有的欢庆都成为浮于纸上的诗与远方。人们难舒眉梢,忐忑不安地盯着那跳动不断的数字,欢声与贺喜鲜绝于耳。
2020就是这样一个年份:困苦之事尤多,沉默之时尤多,但希望也亦尤多。居家不出的日子清闲而漫长。从腊月严冬的酷寒,到暮春青芽的勃发,没有市商之喧闹,亦乏案牍之劳行。在个体清居的生活中,许多人都是一个沉默的思考者。一时间脱离了人世的繁杂,复归见素抱朴的本真。太多的年轻人都执迷于梏于高阁之中的闲适,就像一束干花漂浮于镜中的水月。在墙角凝视一朵孤芳,拾掇起脚下的画笔,重翻起历经岁月尘螨折旧无多的书,看着皂角融化在盆面锻成的光弧。我们擅长于在倥偬之中度日,但当真正的清闲来临时,却又只感怅然若失。
窗外的瘟情,渐渐不再像年关那样吃紧,窗内的2020,脱胎于百无聊赖的沉思。我在山野炊鸣中听着渔樵晚歌,开始了我的创作。静谧的时光悠悠荡荡,像是山寺的古钟,暮作晨发,给予了我千百年前的愁绪豪思。
暮春5月,国内疫情息止,万千学子登上川流的列车,返回校园。我终于踏上了回杭的路,凝望着车窗外汹涌流淌的衢江,听不见流水的声响,却无人质疑它复苏的脉搏。衢江在严冬与早春漫长的等待中独善其身,此刻,终于有鱼儿跃然水面之上,终于有钓客垂钓于江中的低坻。
悠悠,会者定离,一期一祈。我看着一路匆匆驶过的千亩河塘,再回首,面前已是飞红流绿的杭城。听他人说,这座城市空寂了数月。我想,不单是这座城,是这个国家,是足之所至的每一片土地,都在悄无声息的庚子中静默了半载之久。但严酷的寒冬并未消逝其苍劲的锐意,反倒是经历过沉默的洗礼,雪水溶解后才益加光辉。呜呼,它不是沉默中的消亡者,它是沉默中的奋进者。
一切又复归寻常,又不那般寻常,面上的口罩似在时时刻刻提醒人们记起那漫长时期的静默。继而发觉,我们所居的2020,沉默才是其恒远的常态:归客行于思绪万千的街道;后生奋笔于白纸黑字的人生大考;医师拾起疫情病患的手术刀;著者在黑沉键盘下敲击的清脆思想……人生的重要抉择,都在沉默中得以决断。
今年金秋,我与她登上水坝,金乌在侧,江天入画。漫天的赤霞有如亮红色的长江,大手一挥,便自西向东奔涌淌过。这幕景色是没有声响的,但却如一幅逆光的卷轴,似意在述说:庚子一年,是沉默的一年,是困苦的一年,但沉默与困苦之下,是心灵前所未有的激荡与力量。
考场窗前,初雪未止,人声渐散,静谧如常。我伫在庚子年的台阶口,慨然回望。
2020啊,且在沉默中归去罢。
毛凌硕(19岁)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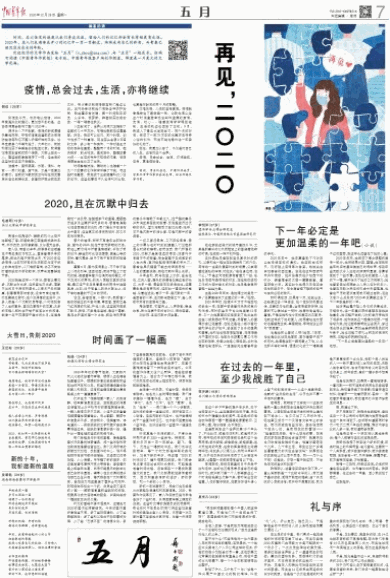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