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母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父亲整日在外蹬三轮车,肩膀上挂着一条湿漉漉的毛巾,穿梭在大街小巷,用踏板上一层层的脚印堆叠成灯下厚厚的硬币。而母亲端坐在学校的小房间里,输入文档、打印试卷,不仅每个月存折上都会多一笔工资,逢年过节还会有米、月饼和油。不过,我从来没见过母亲的钱,她一直把它存在银行里,走亲戚、随礼都是用父亲挣来的碎银子。母亲告诉我,存折里的钱是家里的本钱,以后我上学、成家都要靠它呢。而她没有说的是,一家人的生老病死,也都合在了那小小的存折里。
第一次用到这个钱,是在小升初。我靠着摇号,碰运气才进入了市里的初中,但因为不是凭实力考上的,所以要交一大笔钱。当我纠结了许久才嗫嚅着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她和父亲一拍即合:“交!”“你能摇上这是喜事啊。这钱就是留给你用的。”她显得毫不在意,没有半点心疼。
第二次用到它的时候,母亲脑出血住院,熬了7天后撒手而去。那个存折又在桌上出现了,我突然觉得它分外讨厌,虽然存着钱,但每次出现都是一副无度索取的模样。它是母亲用一辈子给家里存下的东西,但它不仅带走了母亲,也向这个家发动了一次次的侵略战争。每一次出现,都是一股暗流涌动。
意识到母亲真正离开了,是在每天早上,起床后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父亲把饭做好留在桌上,便匆匆忙忙出门蹬车了。到了晚上,卫生间里空荡荡的,不会再有人提前帮我摆好小凳子、棉拖和热水瓶,倒上小半盆冷水,等待我洗脚。我一件件地拾起曾经被母亲包揽的事情,一点点地在屋子的空间里重新构建家的骨架。
姨母经常告诉我,家是一个三角形,父母和我各占一个角,才让家形成了最牢固的结构。
母亲在的时候,她占着一个顶点,收容着我和父亲的棱角。每次父亲发火,提着扫帚往我身上打的时候,母亲往往先在旁边帮腔,训斥我几句,觉得我受的惩罚已经够了,便又去阻拦父亲。她时常在我和父亲的房间来回走动,给我们足够的缓冲空间,把家里暴躁的温度降低,然后一点点地打通两个人间的沉默。
母亲虽然残疾、瘦小,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在我们家说话的分量却是最重的。因为她不仅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而且精通着家里所有的家具,所以她也是所有家具的综合体。母亲是洗衣机、缝纫机、收音机、油烟机,当然,也是戒尺、润滑剂和红花油。她把最绵长的深情都给了这个家,把它打理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这也是为什么,有一次我和父亲发生争吵后,在作业本上愤然写下“家是一个大火炉,把人烧得不想待下去”时,她没有打我,而是对着我呜呜地哭了出来。那时候我上三年级,情不自禁地也跟着哭了出来。第一次,我对家的意义有了分外深刻的认识。
而母亲走后,我和父亲成了相依为命的关系。三口之家缺了一个角,我们默契地把棱角变得很钝,嵌套成火车车钩的结构,拖拽着彼此,也被彼此牵引。我们再没发生过战火,因为母亲始终坐在相框里,靠着墙,微笑着望着我们。我们也时常会谈到母亲,谈到她的抠门,谈到她被人骗的憨傻,谈到她命途多舛的一生。前些日子,看了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我突然觉得这句诗尤其适用于形容母亲——温柔和善,在岁月的一隅泛着盈盈的微光,即使已经离开人间,但掬一捧水,依旧能看见她满是爱意的眉眼。
仇士鹏(22岁)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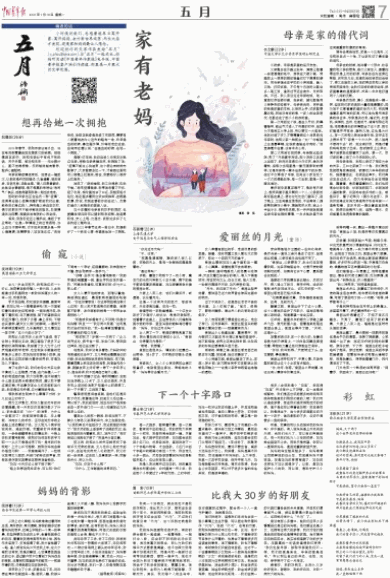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