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长大的你,还记得自己的童心吗?年龄一点点增加,我们或多或少会被磨去一些棱角,但藏在内心角落的那颗童心,可不要让它彻底被埋没。童心是真实,更是珍宝,会让成长中的你,看到不一样的精彩。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蓝色大海的梦境(小说)
王彤乐(22岁)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学生
张老师的手背在身后,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反复吟诵着杨万里的诗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吱呀晃动的风扇不断把燥热的气息往窗外赶,遥山镇的夏天已经来了。
叶小秋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双手托腮数着桑葚树上飞来的麻雀,同桌贾明明趴在桌子上就要睡着了。张老师读完诗,喝了几口水,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蓝色大海的故事。孩子们的心像透亮的浪花被又一次激起,窗外是连绵的山和此起彼伏的绿。
叶小秋想起了妈妈。妈妈在一座海滨城市里工作,很久才回遥山镇看她一次。每次离别前夜,小秋总要妈妈跟她讲许多关于大海的童话,“等小秋长大了,妈妈也带小秋去看海”。天蓝色的许诺里,小秋无数次地憧憬,那些涌动的蓝色有多美,遥山镇以外的世界又有多大。
下课铃响起的时候,贾明明揉着惺忪的眼睛从桌上抬起头来,“上课可真无聊啊”,他伸着懒腰拽了拽小秋的辫子,“笔记借我抄一下咯”。
“你想不想去看海啊?”小秋递着笔记本问道。“看海,你有没有搞错哇,我们这离大海有多远。”明明觉得不可思议。“可我妈妈说大海特别美。”小秋低下头小声嘀咕。“我爸爸也说过,很多年前他也看过大海,后来常常跟我提起。”前桌林佳也转过身来,“我们就一起去嘛,想办法总可以的”。
张老师正坐在讲桌前聚精会神地批改课堂作业,于是小秋、明明、林佳三人提着书包悄悄跑出了教室。山坡上白羊在吃草,牧羊的老爷爷用草帽盖住脸睡在树荫下。
要坐火车去看海肯定得有钱买票。几只百灵鸟飞过天空,抖落下些轻白漂亮的羽毛,小秋提议去森林里多捡些羽毛,拿到镇里卖。没过多久,他们就背着满满一大书包的羽毛来到了遥山镇的集市上。
夕阳染红了小半边天空,可羽毛一根都没有卖出去。小秋叹气道:“那我们就走路去看海!”河岸边摆渡的老爷爷把他们带到岸的另一边,“小朋友们过河做什么?”蓝色湖水里淌着隐约红色的余晖。“我们想去看海。”林佳抢先回答道。“哈哈,看海,你们知道大海有多远吗?”“反正我们会去到的。”小秋撇了撇嘴,在心里倔强地说。
“天黑了就快回来,小朋友们别玩太晚了。”摆渡的爷爷划着桨,笑呵呵地说,“我们大山里的河水啊,一点也不比大海差呢!”
下船后,明明走在最前面,夜莺开始歌唱。天凉下来,山风簌簌作响,穿山而过的火车长久地鸣着汽笛,明明挥着书包,试图让火车等等他们。可火车太快了,每一个车厢都紧拉着蓝色的窗帘,没有人探出头来注意到遥山镇里这三个筋疲力尽渴望去看海的孩子。
天空中蓝色不断下沉,起风了。“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啊?”林佳走得越来越慢,在一堆稻草垛下蹲了下来,蜷起身体,小秋和明明也停了下来,他们靠着彼此的肩膀取暖。田野里的稻草人好像在风中舞蹈,更远一点的地方,小草屋里零星的灯光一盏一盏熄灭。
“你们害怕吗?”小秋坐在明明和林佳之间,问大家,“我们明天要是回不去学校,也看不到大海,该怎么办啊?”“那我们就继续走,走到世界的尽头。”三个孩子昏昏欲睡,三颗小小的纯真的心紧紧挨在一起。
梦中是蓝色的大海,寥若晨星的船在他们梦的边缘航行。月亮是颗黄色的水果糖,黑暗里的紫葡萄已经成熟。他们驾乘的蓝鲸在海浪里跃然而起,满身水汽,披着蓝色的雾。海浪弹奏出更多童话里的乐章,岛屿里的花瓣凋落又重生,遥山镇里的星星在海面上闪着蓝色的光芒。
直到一束亮黄的光照向贾明明的眼睛。他的爸爸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举着手电筒站在眼前。“这么晚了不回家,你们在这做什么?!”贾叔叔好像非常生气,明明蜷在草垛下,又怕又冷,一言不发。
叶小秋看到,妈妈跟在张老师身后也匆匆跑了过来,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一场梦。
“还好没跑到米香镇,不然可就麻烦了。”小秋妈妈在一旁焦急地说着。原来他们走了这么久,连遥山镇都还没有走出呢,世界有多大,大海又有多遥远,小秋觉得不可思议极了!
“小秋,快和妈妈去赶火车。”张老师把叶小秋拉起来,转身对她妈妈说,“还好没耽误了时间,你们快走吧。”
原来,跟着妈妈去城里治病的外婆,这些天病情又恶化了。妈妈放下工作,匆忙地赶回来想要带小秋过去再看看外婆。小秋这才发现,妈妈的眼睛红红的,拉着她的手也冰凉如水。
遥山镇今晚的最后一班火车就要开来了,终点是遥远的海滨城市,小秋和妈妈坐在那列绿色的铁皮车里。火车穿过山岗,跨向大桥,小秋掀起蓝色的窗帘,月色明朗。她想到外婆,想到月色下外婆晃着芭蕉扇给她讲过的人鱼公主的故事。
贾明明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眯着眼睡,张老师牵着林佳绕过哗哗作响的杨树林,他们被同一轮明月照着,奔往遥山镇里几处不同的灯火。而小秋也见到了大海,她穿着蓝色连衣裙捡拾贝壳海螺,并天真地祈愿看到人鱼公主的尾翼。
再次回到遥山镇的时候天色已然入秋。透亮的蓝色变成薄薄的翅膀,在张老师念着乏味古诗词的窗外徘旋。那些梦境在孩子们洁净而坚贞的心间猛烈涌动之后又渐渐归于平息,变得遥远而辽阔。
---------------
青桃
王璐琪
春末夏初的空气被太阳烤得体积膨胀,直至夕阳余光散去,还热腾着。晚饭后,睡觉前是弄堂里的小孩出来玩的时间,孩子数量多,发出的嬉闹声波澜壮阔,也正是因为孩子多,一些小商贩担着自家的商品,地上铺块布,或瓜果桃李,或塑料玩具,或纸笔本子。
悠长的叫卖声在细碎的孩童玩乐声中穿梭,趁着温柔夜色,宛如春季落幕前的挽歌。
有个卖桃的人,脚底下搁一只篮子,篮子里码着一堆桃,并非培育出来的多汁柔软的水蜜桃,而是自家院子里长的青桃。桃在初长时要掐掉一些,好让营养只供给有望长得更大的桃,他应该没有掐过,而是贪心地都留了下来,以至于他的桃个头萎缩,只有杏般大小,且青红相间,蒙着一层浑浊的毛。桃气芬芳,但他的桃一股涩气。
他沉默寡言,别人用电喇叭录了叫卖声,反复播放,他揣着手蹲在地上,一声不吭,看孩子玩游戏看入迷了,跟着咧嘴笑几声。夜色将至,路灯未亮,他的面孔模糊不清,只看得见一排白牙齿,知道他是在笑的。
他五十多岁,跟母亲住在弄堂中段,桃是他母亲种的,他没媳妇也没孩子,大人们叫他“老梆子”,起初孩子也跟着叫,后来被大人骂,才知道“老梆子”是骂人的话。但大人们谈及他,仍旧一口一个“老梆子”叫得利索。弄堂里的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孩子说脏话还是要管。
桃几乎没人买,他不急也不燥,屁股稳稳当当坐在马扎子上,看孩子蹦跳,这一批桃放软和了,放不住了,再放到次日要烂掉,又无人买,便分给热得满头大汗的孩子们。他把筐拎到一家人的水龙头前,这家的水是用抽水机抽上来的地下水,比普通水温度低,一筐青桃淋了冰冰凉凉的水,也并没有变得更好吃,洗得再干净,咬一口舌头也麻麻的,仿佛褪不净的桃毛扎进了肉里。
分完这一筐软桃,第二天他仍旧坐在原处看我们玩耍,筐里盛着新摘的青桃,码放整齐,一共四排,每排八个,小而局促。因他在旁边看着,便成了公正的法官,谁违反了游戏规则,不服气的人手一指,“不信问他,他看着呢。”
他便当真站起来,走到孩子们中间,把所看到的掰开揉碎讲一场,力证正义的一方。
他的确看得认真,没有偏差。
那是个普通的傍晚,他坐在马扎子上,与隔壁摊位的人说话,忽然有人喊,你妈上厕所摔倒了。他慌得站起来就往家赶,两边摊位上的人也跟着他后面跑,我们停下来,只见在外头吃饭的大人们放下碗筷,涌向他家门口。羊肠子一样细的弄堂堵住了,不一会儿,等不及救护车,六个人抬着他的老母亲出来了,他的老母亲卧在躺椅上,男人们手抬着椅子腿,大声驱赶着我们让路。
一切发生得突然,结束得迅速,我们只从人缝里瞥见他老母亲的白头发,没有光泽的白脑袋枕在竹枕上。
孩子善忘,待人群散净,继续着游戏,天完全黑了,开始有孩子被陆续喊回家。我们这才发现平日里的商贩今天意外地都走了,只剩下他孤零零的筐和马扎子。
“他的桃忘了拿回去了。”一个大孩子喊。“那我们等他回来吧。”一个女孩子回应。
于是我们围着筐挨个坐下,抱着腿等他,弄堂口望了又望,熟悉的身影并没有出现。
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远远叫我们赶紧回家,声音急促,我们也察觉到今天气氛的不正常,害怕惊惶却不知为何。天空颜色越发深了,靛蓝得犹如被水冲洗过。我们从未在外面玩这么晚过,有了想回家的念头。
“放在外面不要紧吧?”
“要不然我们给他送回去吧?”
“我们吃了吧?”
最后一个提议不错,但很快被我们当中最有主意的孩子否决了。“他又卖不出去,每次不都给我们吃吗?”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搬着马扎子,抬着筐,把桃给他送了回去。走得匆忙,他虚掩着门,通风不好,从门缝里散发着一股长年累月发酵的菜油味,院子幽暗,大桃树黑黢黢地立着,夜幕给它的枝丫修剪得如同木刻画。
我们把桃和马扎子放在他的树下。正要走时,忽然大孩子说,桃少了一个。伸头看看,因为桃码得整齐,最左边的确少了一个。
于是我们开始自查,在大孩子的监督下,乖巧地把手摊开,最后桃在最小的那个孩子的兜里找到了,他被迫把桃拿了出来,递出去的时候又不舍得,紧紧攥在手心里。
是我把他的手掰开的,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小胖手,没骨节似的绵软,手心里捏着一只完全没熟的青桃,一点儿红影子都没有,在手里攥久了,被手汗浸得湿漉漉的,桃毛全磨掉了,夜色下青翠得剔透,仿佛一颗宝石。
放回桃子中央,它看上去很不一样。树上还有许多毛桃,隐在树叶丛中,等着明天的夏季阳光给它们染上红。
---------------
细语童年
姜士冬(22岁)长春师范大学学生
那时候,一天很长,太阳落下得慢,将云朵都染成了红色。那时候,晚上还能看到大片的星星,亮闪闪的,夜空下的我哼唱着歌谣。那时候,我还是小小少年,对这个世界抱有大大的幻想。
童年是不声不响离开的,我没有来得及与它道别。想来,长大后的许多道别,都是不声不响的,悄悄离开,悄悄归来,不需要太多的语言,语言往往很苍白无力。当我意识到童年已逝,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抱抱还不想长大的自己。
感谢上天,赐予我一个美好且完整的童年,在乡村初生,在乡村长大,我喜欢光着脚丫在土地上行走,仿佛自己落地生根,回归大地。
村子不大,约有一百多户人家,与我同龄的小伙伴也就七八个。我们一起去村东头的小学上学,一起玩游戏,就连偶尔打架,也都是我们几个。小孩子嘛,没有深仇大恨的,几天后又成了好朋友。谁都不再提打架这件事,就好像打架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童年的夏天是美的,院子里的菜花都开着,就连果树的枝条上,也开着各种颜色的花儿。奶奶喜欢种花,将院子的前前后后都种满了花。花都开了,姹紫嫣红的,蜜蜂在嗡嗡嗡地采蜜,蝴蝶在院子里相互追逐。下过一场雨后,天边还会出现七色彩虹。
奶奶指着彩虹对我说,那是天上下雨,淋湿了仙女们的衣服,于是呀,仙女们就搭起彩虹色的晾衣竿,在晾衣服呢!年少无知的我,竟然信以为真。后来有几次下雨,雨过天晴后却没有出现彩虹。我问奶奶为什么没有彩虹呢?奶奶回答,那是仙女们都没有外出,没有淋到雨,自然不用晒衣服了。
小时候多傻,对很多事情都深信不疑。家里养了十多年的阿黄老了,牙都快掉光了,见到生人也不会汪汪叫了。有一天,阿黄连早饭都没有吃,我叫它,它没有理我。我知道它听到了,因为我叫得很大声,一定是它在装睡。
等我放学回家后,发现狗窝里的阿黄不见了。我问奶奶,奶奶说仙女瞧见了阿黄,很喜欢它,就把阿黄接到天上去了。能到天上去自然是好的,我叹了一口气,心想要是早点回来就好了,说不定还能看到仙女长什么样子。
我自然相信仙女的存在了,我读过《西游记》,那里面就有很多仙女,还有会使用金箍棒的猴子,十分贪吃的猪八戒。我总会抬着头,呆呆地望着,盼着能见到仙女。天空中的云朵变换着模样,有时候就有一朵长得很像仙女。
是不是当我知道这世间没有仙女的时候,我的童年就结束了呢?后来,离开乡村,去了城里继续念书。我发现夜空中的星星少了,就连北斗七星都不能常见了。城市的夏天很热,密不透风的热,少了花香,也不见相互追逐的白蝴蝶。
昨夜,我梦到了仙女,她的衣服被雨淋湿了,她搭起彩虹桥,晾起了衣服。奇怪,怎么没见到仙女身旁的阿黄呢?一定是偷跑到哪里玩去了。醒来,窗外的雨下得淅淅沥沥,有几声狗吠,我却叫不出它的名字。
---------------
我的“幼时记趣”
张喆(24岁)物理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初中背古文的时候,我们都曾背过一句“余忆幼时,能张目对日”,当时看着文中的“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或“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只是觉得拗口难背,长大了再看,倒是能从里面看出几分乐趣和与自己童年的相似处来。
如果把过往的时光写成一本书,那我并不是一个好的记录者和收藏家。和朋友聚餐时,我们也会围坐在一起说说小时候,可是很多次,我努力摇晃着记忆的存钱罐,从小小的开口掉出的却不是连续的童年记忆,而只是几块斑斓的碎片。很多次,我就是随手翻检着这些碎片,试图拼凑起完整的从前。
其中的一块碎片里,藏着一捧幼时的雪。北方的孩子对于雪从不陌生,从小我们就熟悉了看它们从天上来,从树上结出的雾凇里来,也从“泼水成冰”的那个小杯子里来。
每次身边陆陆续续有同学因为感冒请假的时候,那就是冬天来了。冬天是奶奶的数九歌和爷爷的大棚,是长长的寒假和热闹的春节,也是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雪。说不准哪天早上起来,地上就早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大人们爬上房顶,一边把厚厚的雪推下来,一边开心地笑:“来年地里肯定虫少!”小孩儿们则挤在屋檐下,乐此不疲地看那些雪的瀑布。那些雪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或者三五成群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铁锨,拍出一个丑丑的雪人;或者戴上厚厚的手套,打上一天轰轰烈烈的雪仗。村里有一块背阴的土坡,雪尤其不容易化,拿上一块厚纸板,那里就成了雪道。大家带着几分运动员的气势在坡顶默契地排着队,比谁滑得更远,也比谁摔得狼狈,“嗖嗖嗖”地滑过一个又一个冬天。
另一块儿碎片里躲着一只狗,那是一只通身长着淡黄色毛发的小土狗。每天早晨,它就会准时用两条前腿扒在炕沿上,把人挨个舔醒,以至于后来爷爷奶奶不得不早起躲过这场洗脸仪式。等放学时,他又会准时在门口等我,连奶奶也感叹:“你说它又不会看表,怎么掐点儿掐得这么准呢?”
还有一些碎片,可能是努力攒钱后买的那张音乐贺卡,送给了小学毕业时分开的朋友,那是第一次用“仪式感”度过离别;可能是充满错别字的一封道歉信,送出去之前还在“自尊”与“友情”之间的纠结中被揉搓得发皱;可能是一下午才赢来的一颗特别好看的玻璃珠,直到现在也舍不得扔,仍旧放在自己的化妆台上……
这些碎片就像拼图里的一个一个小块儿,拼凑不出完整的童年,只拼成一个长大的我。我努力从这些残缺的画面中窥见了童心的一角,那是爱着生活的一切、也被一切爱着的一角。
现在的我们已经努力长成了大人,也许我们没能成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那个未来的自己,但是没关系,我们经过的那个童年,就像是一个温柔又充满无限可能的春天。而现在的我们保持童心,就是春天已经走了,我们也还是能怀抱着发芽的心情,打开一本崭新的“幼时记趣”,并郑重地写下几个大字:正在记录中。
---------------
童年的小岛
李霜氤(30岁)上海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生
那岛屿终日被平静的水域包围着。水面通常清澈如镜,偶尔被不知名的力量翻搅起深海底部的泥浆,水就变成了黄色,浑浊不堪。但平日里,雨后的阳光轻轻抚弄摇曳的植物,有几分婀娜。
游人乘着绿色柔软的船来到这里,亦可在高大的绿色植物下小憩。若来的是文人墨客,便可吟诗作对,将细碎的灵感刻录于植物的表皮,或者质地坚固的沙砾。那些思绪的碎片,或许会随着岁月风化消失,也许会幸运地留下来,万古流芳。
这是一处名胜之地,游人找到它亦需要机缘。通常需要一场雨,还有一个独具匠心和童心的人……
“你们快来吃饭,别再玩泥巴和蚂蚁了!”一个来自现实世界的大人声音把我从这个现实的梦境里拉回来。是姨妈的声音,因为一些原因,这个假期我要寄住在这位远房姨妈家里。
去年差不多也是这样。去年,姨妈的儿子、我的表哥教我用泥巴来构筑城堡,还教我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例如突兀尖顶的哥特式、圆而优雅的巴洛克式,等等。表哥说,他长大想当建筑设计师。那时候,我坚定地认为,表哥长大后会如愿以偿,设计出漂亮而别具一格的建筑。
我回头,看见表哥背着书包,面无表情地走进屋子里。
自从参加补习班,表哥再也不陪我玩泥巴了。即使是表哥放假的时候,我也不敢提让表哥陪我玩泥巴。我怕表哥会一边拒绝我,一边眼神中流露出“我不要玩这些小孩子的玩意儿”的神情,那是我不愿意面对的。
吃完饭,我回到了院子里。刚刚下过一场雨,我用泥沙堆起的“小岛”被带着泥土味的水包围住,上面的小草也被水珠压得轻轻摇曳。我把几只蚂蚁抓到一片青翠的叶子上,让它们乘着叶子船,去岛上“探险”。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我忍不住吟诵起李白的诗。
我出生的城市虽然地处沿海,我却很少看见海。我家乡的海边也没有椰子树。我仅仅在杂志上看见过高大婀娜的椰子树,金光闪闪的海滩,还有载满游客的船。眼前这小小的墙角和我童年的小岛,是我最向往的梦境。
蹲在墙角看了一会儿蚂蚁后,我回到屋子里,正好看见姨妈在训斥表哥。
“你呀!就这样不努力,这么简单的题都错,以后成绩不定差到什么程度。长大能干吗,喝西北风吗?”
我看到表哥低着头。
多年后,表哥说过,他不喜欢数学,可偏偏他的妈妈就是数学老师。表哥被姨妈批评不断,逐渐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如果当时的他知道,学好数学对成为一个建筑师很有帮助,或许他不会那么讨厌数学吧。
可惜,当年没人告诉他。
没人陪我玩,我便自己读着表哥的书。读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惊奇地发现,鲁迅先生的百草园、赤练蛇、覆盆子、蟋蟀,和我的蚂蚁、树叶、椰子树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我拿着课本,跑向刚刚备课完在灯下小憩的姨妈。
“姨妈,我特别喜欢这篇文呢!您家的院子,多像那百草园啊……”
姨妈似乎倦了,微笑一下,合上面前的书本,对我说:“鲁迅先生是大家,我们普通人哪儿能比呢,我可看不懂这些。”
那一刻,我非常希望能穿越时空,去找鲁迅先生一番倾谈。我相信,他会懂我的小岛。可惜,现实中没有时光机。
从姨妈的书房出来,我也合上书本,关掉灯,爬上床铺。
第二天清晨,我又望向我的小岛。水似乎蒸发了不少,树叶小船也搁浅在了水泥和红砖旁边,蚂蚁们不知所踪。阳光正烈,不一会儿,院子里的水就干了。
表哥已经背上书包,前往补习班……
多年后,表哥考上了大学,可惜离他的建筑学专业差几分,于是选择了会计专业。他对专业也算满意。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他当建筑师的梦想,但我始终记得我的小岛。
---------------
童心便是喜欢歌唱
戴霆宇(23岁)法国尼斯索菲亚大学学生
喜欢卡片、玩偶、有耳朵的帽子
喜欢把人间的细语对万物表达
交换、释怀目光里的坚硬与晦涩
我喜欢的事情是刻写年轮的笔
曾经被成长浪费的笔墨
在可爱的概念中
把标点藏进时间,装点童话
请所有的美好搬进城堡
在窗边,花花草草尽展歌喉
把影子晾晒后铺成被子
用梦为世界盖上柔软的印章
在人的背后,重新长出了翅膀
除了童心,我找不到更美好的词语
能配得上玫瑰花上的露珠
以及你眼中蠢蠢欲动的晨曦和鸟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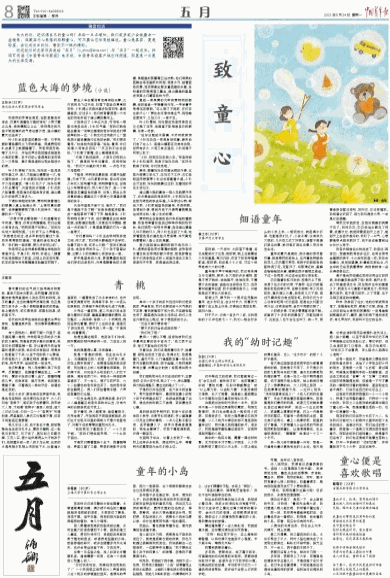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