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初的空气被太阳烤得体积膨胀,直至夕阳余光散去,还热腾着。晚饭后,睡觉前是弄堂里的小孩出来玩的时间,孩子数量多,发出的嬉闹声波澜壮阔,也正是因为孩子多,一些小商贩担着自家的商品,地上铺块布,或瓜果桃李,或塑料玩具,或纸笔本子。
悠长的叫卖声在细碎的孩童玩乐声中穿梭,趁着温柔夜色,宛如春季落幕前的挽歌。
有个卖桃的人,脚底下搁一只篮子,篮子里码着一堆桃,并非培育出来的多汁柔软的水蜜桃,而是自家院子里长的青桃。桃在初长时要掐掉一些,好让营养只供给有望长得更大的桃,他应该没有掐过,而是贪心地都留了下来,以至于他的桃个头萎缩,只有杏般大小,且青红相间,蒙着一层浑浊的毛。桃气芬芳,但他的桃一股涩气。
他沉默寡言,别人用电喇叭录了叫卖声,反复播放,他揣着手蹲在地上,一声不吭,看孩子玩游戏看入迷了,跟着咧嘴笑几声。夜色将至,路灯未亮,他的面孔模糊不清,只看得见一排白牙齿,知道他是在笑的。
他五十多岁,跟母亲住在弄堂中段,桃是他母亲种的,他没媳妇也没孩子,大人们叫他“老梆子”,起初孩子也跟着叫,后来被大人骂,才知道“老梆子”是骂人的话。但大人们谈及他,仍旧一口一个“老梆子”叫得利索。弄堂里的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孩子说脏话还是要管。
桃几乎没人买,他不急也不燥,屁股稳稳当当坐在马扎子上,看孩子蹦跳,这一批桃放软和了,放不住了,再放到次日要烂掉,又无人买,便分给热得满头大汗的孩子们。他把筐拎到一家人的水龙头前,这家的水是用抽水机抽上来的地下水,比普通水温度低,一筐青桃淋了冰冰凉凉的水,也并没有变得更好吃,洗得再干净,咬一口舌头也麻麻的,仿佛褪不净的桃毛扎进了肉里。
分完这一筐软桃,第二天他仍旧坐在原处看我们玩耍,筐里盛着新摘的青桃,码放整齐,一共四排,每排八个,小而局促。因他在旁边看着,便成了公正的法官,谁违反了游戏规则,不服气的人手一指,“不信问他,他看着呢。”
他便当真站起来,走到孩子们中间,把所看到的掰开揉碎讲一场,力证正义的一方。
他的确看得认真,没有偏差。
那是个普通的傍晚,他坐在马扎子上,与隔壁摊位的人说话,忽然有人喊,你妈上厕所摔倒了。他慌得站起来就往家赶,两边摊位上的人也跟着他后面跑,我们停下来,只见在外头吃饭的大人们放下碗筷,涌向他家门口。羊肠子一样细的弄堂堵住了,不一会儿,等不及救护车,六个人抬着他的老母亲出来了,他的老母亲卧在躺椅上,男人们手抬着椅子腿,大声驱赶着我们让路。
一切发生得突然,结束得迅速,我们只从人缝里瞥见他老母亲的白头发,没有光泽的白脑袋枕在竹枕上。
孩子善忘,待人群散净,继续着游戏,天完全黑了,开始有孩子被陆续喊回家。我们这才发现平日里的商贩今天意外地都走了,只剩下他孤零零的筐和马扎子。
“他的桃忘了拿回去了。”一个大孩子喊。“那我们等他回来吧。”一个女孩子回应。
于是我们围着筐挨个坐下,抱着腿等他,弄堂口望了又望,熟悉的身影并没有出现。
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远远叫我们赶紧回家,声音急促,我们也察觉到今天气氛的不正常,害怕惊惶却不知为何。天空颜色越发深了,靛蓝得犹如被水冲洗过。我们从未在外面玩这么晚过,有了想回家的念头。
“放在外面不要紧吧?”
“要不然我们给他送回去吧?”
“我们吃了吧?”
最后一个提议不错,但很快被我们当中最有主意的孩子否决了。“他又卖不出去,每次不都给我们吃吗?”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搬着马扎子,抬着筐,把桃给他送了回去。走得匆忙,他虚掩着门,通风不好,从门缝里散发着一股长年累月发酵的菜油味,院子幽暗,大桃树黑黢黢地立着,夜幕给它的枝丫修剪得如同木刻画。
我们把桃和马扎子放在他的树下。正要走时,忽然大孩子说,桃少了一个。伸头看看,因为桃码得整齐,最左边的确少了一个。
于是我们开始自查,在大孩子的监督下,乖巧地把手摊开,最后桃在最小的那个孩子的兜里找到了,他被迫把桃拿了出来,递出去的时候又不舍得,紧紧攥在手心里。
是我把他的手掰开的,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小胖手,没骨节似的绵软,手心里捏着一只完全没熟的青桃,一点儿红影子都没有,在手里攥久了,被手汗浸得湿漉漉的,桃毛全磨掉了,夜色下青翠得剔透,仿佛一颗宝石。
放回桃子中央,它看上去很不一样。树上还有许多毛桃,隐在树叶丛中,等着明天的夏季阳光给它们染上红。
王璐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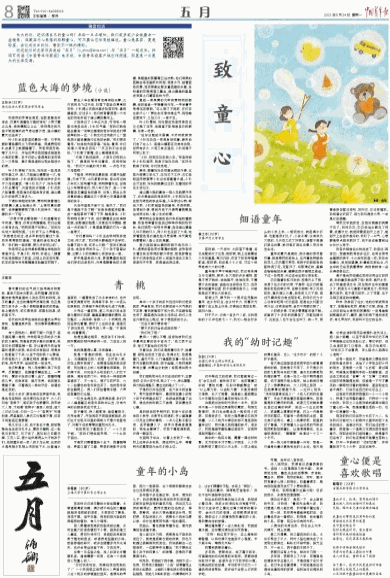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