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爱一个人要付出多少?你为她(他)的付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不管是爱情,还是父爱、母爱、友爱,每一份为你付出的爱,你可曾珍惜?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一句“姐姐”的重量
余湘(23岁) 上饶师范学院学生
2017年,3月的最后一天。我在妈妈口中,确认了你的存在。妈妈说,这就是命,语气又幸福又惆怅。谁能想到呢?在妈妈尚且平坦的肚子里,有个小生命在悄无声息地长大。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生命中的所有美好,我都愿意和你分享。是期许也是承诺。入睡时,我想象着你的样子,模模糊糊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好梦,梦里有人奶声奶气喊我“姐姐”。
随着妈妈的肚子一天天变大,我意识到自己也在悄悄改变。我更加努力地念书,三更灯火五更鸡,一心想考一个好大学;更加体谅妈妈,收起青春期那些无谓的锋芒,有空就帮忙做家务。长大似乎是一瞬间的事情,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不再沉溺于青春期梦幻般的怀想,学着做好眼前的事:弄懂一道数学题;作业写完了帮忙拖地;还剩一点零花钱,给妈妈买一个小蛋糕。
是的,你大概不会明白,我在学着如何做一个姐姐。“姐姐”这个称呼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弟弟,遗憾的是,我和弟弟从小不在一起长大,相处起来有些隔阂。我希望这样的遗憾不会再有,虽然隔着近20年的距离,但血脉相连的我们足以跨过年龄的鸿沟。
9月,是收获的季节。在这个9月,你毫无预兆地出生了。上天垂怜,你和妈妈都平安无事。不过直到在医院亲眼看见你,我才把担心焦虑抛诸脑后,一颗心落到了实处。
你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了头和一只小手。以前听老师说,小孩子刚生下来都是不好看的,我看着你,觉得老师说的并不一定都对。你躺在妈妈身边睡着了,小小的脑袋歪着,眼睛紧闭,脸红红的,一只手握成小拳头,像树上的蓓蕾,也像初生的嫩芽,是一切希望的开始。
我问妈妈,你为什么那么小?妈妈笑着说,刚出生都是这么小。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小得不可思议,小脸还不如我巴掌大。我看了又看,想把你小小的样子刻入脑海。我已经能够预想到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你一点点长大的样子。你会如何叫我“姐姐”呢?唤一句“姐姐”,两个字轻拿轻放,像一片云,缓缓降落在了心上。一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就被巨大的幸福感充盈着。我靠近你,听到你的呼吸,呼哧呼哧的,有些急促。我想亲亲你,但你睡得很熟,怕吵醒你,就只是拿自己的大拳头碰了碰你的小拳头,默念道: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呀。
从四口之家到五口之家,喜悦并没有持续下去。我渐渐明白,“姐姐”这两个字不只是一句如云朵般的呼唤,云朵背后承载着的重量,无法计算。
你还那么小,万事都需要照顾。还不会走路时,整天就是吃奶和睡觉,你睡不安稳,必须要有人一直抱着,一旦放你到床上,马上像触动了什么开关,惊天动地的哭声随之而来。没办法,只能抱着。妈妈抱累了就换我抱,你一点也不重,但一直抱着,难免手臂酸涩。那时我总想着,你再长大一点,会走路、会说话就好了。殊不知,等你会走路了,更是闹得家里鸡飞狗跳。家里各处都散落着你的玩具,每天都能听到你的哭闹声,交织着妈妈的呵斥声。
刚出生时的美好幻想碎成一地,你的确如期长大,但我并不如想象中幸福。一句“姐姐”的重量,远比想象中沉重。我要忍受自己来之不易的独处时间被你打扰,原谅你把我珍藏的书本撕得稀烂,还要耐心十足地追着你,把一碗饭喂完……这些琐碎的小事让我感到疲惫,更心疼的是妈妈,她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你。妈妈好像就是这样变老的,在吱呀吱呀的缝纫机声中,在无尽头的家务里。
有时候会想,如果没有你,我是不是会活得更轻松一点?我不必考虑把自己喜欢的专业换成稳妥的师范专业,不必省吃俭用为你买零食,不必把难得的假期“浪费”在你身上。回过头看,其实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这也不是做姐姐的义务,但我就是忍不住想到未来,等你长大,父母年迈,我总是要出一份力的。这不存在牺牲,也不苛求回报,不过因为你喊我一句“姐姐”,而我们是家人啊。
当然,那个念头只在对你感到崩溃时出现。大多数时候,我总是幸福的。在你第一次咿咿呀呀喊我“姐姐”的时候,在你把心爱的零食特地留给我的时候,在每一次你乖乖地按时吃完饭的时候。对于你,我偶尔感到崩溃,时时觉得治愈。
就在前几个月,我的考研成绩出来,分数比较低,加上考驾照失败,心情低落,就想自己静一静。你屁颠屁颠过来,要我给你洗脸洗脚,还要我哄你睡觉。我极不耐烦地帮你洗好脸,陪你洗脚。洗脚时你故意把水溅得到处都是,见我惊呼就哈哈大笑,玩得更起劲。溅到脸上的洗脚水是压倒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怒气十足地吼:“你要玩到什么时候!”情绪爆发,我忍不住流下眼泪。
笑声戛然而止,你蔫蔫地低下头,很小声说,对不起,不要生气。我赶紧放低声音解释,不是在生你的气,是生姐姐自己的气。说着说着,又滚落下眼泪。你看着我,还洗着脚,突然站起来,用你小小的手抱了抱我,如同很多次,你摔跤哭泣时我将你抱在怀里。我闻到你头发上肥皂的清香,你的身体热乎乎的,像个小太阳,我感受到了你的安慰和传递过来的能量。你说,姐姐很厉害,姐姐考得上。
我的眼泪掉得更凶了,那种幸福感再次充满了我的内心。哎呀,那个小小的蓓蕾开花了,嫩芽儿也开始长大啦!
——————————
母亲肩上扛着的梦
孙元熊(23岁)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学生
2020年的春天注定难以忘却,回想起那段居家防疫的日子,每日与母亲的相处让我更加体会到母爱常驻心间。忍不住静而思之,忆起往事。
从我知事的年岁开始,母亲的身影就一直忙碌于厨房、庭院、田野,每一处都有她留下的脚印和汗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柴米油盐中寻找希望的点滴,那些无言的酸楚,某个瞬间,便会变成一个缩影。她的生活,仿佛被时间禁锢,日复一日地循环,不知疲倦。长大后,我开始模仿母亲背起生活的行囊,在多种角色的转换中,褪去往昔的稚嫩。然而,母亲一直都是母亲,忙碌的场地没有变,早起晚睡的习惯没有变,只是,很快弯了腰,白了发。
天色微明,鸡鸣打破了村庄原有的安详、静谧,青色屋顶上的炊烟袅袅升起。厨房里又传出熟悉而温暖的声音,我被一阵香醇的气味熏醒。大约七点钟,阵阵脚步声在耳畔回响,早起,是母亲的习惯。她轻轻推开房间的门,手中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放在桌上:“记得吃早餐,我去地里干活儿了!”母亲悄然掩门而去后,我走进厨房,电饭煲里的馒头和鸡蛋正冒着热气儿,电壶中的热水也已灌满,向我源源不断地输送爱的能量。
在网课完成后的闲暇之余,我前往地里探望母亲,顺便带些吃的。她已经锄了六七垄,脸上的汗珠在流淌,衣服湿透了。趁母亲休息时,我接过她手中的锄头,一股蛮劲儿地向前刨。也就十多分钟,双手开始酸痛,体力明显不如以前,望着广阔无垠的地面,眼前闪现一道光晕,昏沉之感瞬间弥漫全身。母亲察觉了异样,跑过来用毛巾擦拭我额头上的汗珠,一副心疼的模样……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我深知种地是生存的根本,也相信汗水扑溅泥土,孕育着丰收的喜悦。眼前这个身材矮小、日渐消瘦,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女人,用一生的辛勤劳动,抚育子女读书是多么不容易。这一刻,我恍然明白,母亲肩上扛着的是关于我长大的梦,这场梦,柔爱之中见坚强。
随着开学的日子临近,母亲将我闲置不用的物品装进行李箱,反复清点,生怕遗漏了什么。不一会儿,箱子塞得鼓鼓的,还多了个装满家乡特产的手提袋。母亲“宁可多带,不能浪费”的生活风格仍然没有改变。小时候,因为不懂世间冷暖,常常埋怨母亲让我携带很多东西,大到床单被褥,小到毛巾牙刷,母亲都舍不得丢弃,常常叮嘱“多带点,万一以后要用到呢!”如今的我渐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在她眼中,我永远是需要被照顾的孩子。
临行前,我直视着母亲,她眼角的皱纹越来越长,黑发中又增添了几许白发。都说岁月是把锋利的雕刻刀,母亲愈发苍老的面容正是这最好的解答,它不断提醒我——母亲已不再年轻了。我心头一颤,没想到刹那芳华之间,我和母亲竟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这样的现实让我不知所措,更让我无比辛酸。
拐角处,母亲定住了,噙着眼泪说:“路上小心点,到学校回电话。”我转身紧拥母亲,用力点了点头。走在村间的小路上,我无数次看见母亲挥手作别时的情景,压抑不住的泪水瞬间落下。沉默中,在缓缓行驶的列车上,母亲的身影渐行渐远。
今夜,月色如水,如母亲手中的掌纹,圈画着她一生的柔情美丽,纹中烙刻血缘的印记,让我与母亲的距离更贴近,让爱常驻心间。
——————————
爱,本就是动词(小说)
冯嘉美(20岁) 武汉晴川学院学生
姑姑退休后常去文化宫里看人家跳舞唱歌,她尤其爱每月的14日,因为会有话剧表演。
我说,他们演来演去无非就是那几个经典的悲情本,演繁漪的阿姨估计都把泪哭干了。
姑姑说,除非她死,她泪才干。
后来,在一个14日,姑姑没有去文化宫,她说,演繁涟的人果真把泪哭干了。
那个阿姨姓连,年轻时从北方来此,听说本来是为看看远嫁的亲戚,没想到将心落在一个本地人身上,便再没有向北方回望了。
我想她是多爱她的丈夫。
连阿姨的丈夫是位剧作家,他们才相识的那会儿丈夫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就靠给三流杂志社投稿来维持生计。
连阿姨呢,是位永远心存梦想的“少女”。她听她丈夫说,他会用作品让她站上省剧院的舞台。
我听到此处连忙摇头,糊涂。
但没想到,丈夫的剧获了奖,要登台巡演,还有投资方想要拍成微电影。
连阿姨那时已经有了两个小孩,她从生活的柴米油盐里猛然抬头,去找她丈夫兑现诺言。
丈夫应允了,和一群所谓业内大佬并坐在观众席上,看连阿姨试戏。
她只有一句台词:“锁都找不到在哪儿?我怎么找钥匙?”
我觉得十分荒唐。
连阿姨也是如此认为,她没办法从这句“来路不明”和看不清情感的词里找到她的表演,毫无疑问她失败了。
自此,连阿姨专心照顾家庭,对表演的想法好像如乍现的火光,只听得响,然后消散干净。我以为会有什么出奇的情节,但没有。她的丈夫很本分地做自己的工作,却再也不过问连阿姨暗暗跳动的心。
日复一日,日日如一日。
在极其平常的冬天里,连阿姨的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她孤身一人后进了文化宫,这里有志趣相投的人。
姑姑形容她表演的那股劲,狠得不忍心看,一把年纪又跪又摔,换作别人早就七零八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架着她。
我听到此处要改口了,她爱的不是丈夫,是埋在心里的梦,像打十年的坐,锤百年的铁,怎么放得下。
“她为什么死?”我问。
姑姑瞳孔颤了颤,凑在我耳旁说:“听人说,她丈夫发病前给她打电话,她却因为看社区里的人演戏而漏接了。”
姑姑又补充,文化宫要被拆除了。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她总爱演那些尽在为他人泪的角色,她是想把十几年的梦与憾哭给世人看,用各样角色的悲去麻木自己。
听她虔诚赎罪的庙宇崩塌,她成无人打捞的失事沉船。
当人不再做梦,心也不会跳了。
我猜连阿姨或许全名叫连漪,和她演的繁漪一样,最后疯魔,命运如暴雨打在地上晕开的圈圈涟漪,她看不清也分不清,哪个圈是她。
年轻的她用勇气孤注一掷,她想,爱什么便成为什么。可是她的爱有些盲目了,像她试戏所说的词暗示的那样,她连锁都找不到,怎么找得到钥匙?
世间万物明码标价,她也为自己的爱付出了“代价”。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在思考,连阿姨到底爱谁?她的丈夫还是她自己的梦想?
可是答案无从考证。
文化宫被炸毁的那天,姑姑从话剧社的团长那里领到一个奖,是表彰连阿姨的,她被评为年度最佳演员。
“太可惜哩,小连知道就好了,她回头和家里说起来不得开心死。”姑姑话里满是遗憾。
可能连阿姨爱的,是回不去的故乡。
她或许当年是要争一份骄傲,但她也为固执与不甘心的爱付出了代价。
我问姑姑我会像连阿姨那样吗?
姑姑说,天地规律有舍有得,但如何衡量“代价”的度,那把秤在于我。
世间有无数个连阿姨,大多可能没有她那般执拗,意难平后就不再追究了。
爱本就是动词,肯定要消耗什么,至于如何标价,自在人心。
——————————
爱的亏欠(小说)
王子怡(24岁)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
走过贴满小广告的楼道爬到六楼,素霞已是气喘吁吁。她将手中的快递放到脚下,掏出钥匙打开自家的房门。窗外的绿树与阳光反衬着房间的破旧与灰暗,林西正躺在沙发上和男朋友聊天。
“下班了,你的快递取回来了。”素霞将快递消毒后拿给林西,林西没有接。“这是给你买的,今天母亲节。”母亲节快乐这句话终究是没说出口。
这是林西工作以后第一次给素霞买东西。起因是同事朵朵说她每个节日都送父母礼物,工作后每个月主动转给他们一半的工资。林西听后发现自己从未给素霞买过礼物,工作后的工资都是自己挥霍,内心有些愧疚,给素霞从网上买了一身衣服和一双鞋子。
素霞听到林西的话惊讶地拆开看了,是一身运动装和一双运动鞋。素霞到镜子前试衣服,颜色有些老气但还是很合身的。“你这孩子怎么乱花钱,我衣服够穿呢,不用给我买。”
傍晚室内灰暗,林西没看见镜子里素霞的脸上满是欣慰。她听见素霞的话感到自己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两件加起来也不到二百块呢,怎么就乱花钱了!以后什么都不给你买了。再说我花的我自己工资,又没花你的钱。”
钱是个敏感字眼,林西从小到大最反感素霞限制自己花钱,她还记得初中时她看中了一条裙子,怎么央求素霞她都不给自己买。她在心里记恨她,埋怨她为什么没有给自己和同龄人一样的生活。她整个青春都在自卑和羡慕别人中度过,她羡慕同学们有很多好看的衣服,羡慕她们过生日时能吃到生日蛋糕。到了大学,面对喜欢的人她不敢接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素霞没能给自己提供好的生活条件,一直舍不得给自己花钱。
林西工作以后理直气壮地安排着自己的工资:高档化妆品、名牌衣服、特色美食、外出旅游。她从未想过用赚的钱给素霞花,素霞也总是告诉她自己的钱够用。
晚饭后,林西放下手机突然说:“我准备辞职去广州和陈翔结婚。”正在收拾碗筷的素霞怔住了,夕阳将最后一抹金黄打在她的侧脸上,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像是一座未完成的雕塑,“广州太远了,我不同意。”
“这都什么年代了,距离还是问题!他对我比你还好,他舍得给我花钱,给我买了很多裙子,我整个衣柜的衣服都是他买的。”
素霞的脸上写满悲伤,“几件衣服就能把你收买了,你从小到大我给你买了多少衣服?他舍得给你花钱,从你出生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你怎么不算算。”
“养一个孩子能花多少钱?你也没给我过花多少钱,我初中时候想让你给我买条裙子你都不给我买。”
“那时候你爸生病了家里吃饭都是问题,我拿什么给你买裙子?你爸没了,我一个人供你念书供你吃喝,什么时候让你饿着过?”
素霞的语气生气又委屈,她叹了口气走出房间。林西望着她渐渐苍老的背影,内心有些触动。窗外夕阳已经消失,黑色如幕布遮盖了整个天空,没有拉灯的房间黑漆漆的。
第二天素霞就同意了女儿的婚事,但她向男方家庭要了很多彩礼,未来公婆颇有微词。林西想素霞那么痛快就答应自己结婚,原来不是为自己考虑,是为了钱。林西赌气没有让她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婚礼。
婚后没几天,素霞就病了,因为疫情林西不能回去探望,丈夫提议给妈妈打些钱。“她手里不是还有彩礼钱吗?那么多钱还不够花?”“你误会妈了,她一直不让我告诉你,我去你家接你那天,妈把那张银行卡又塞给我,她说你远嫁她不放心,要这么多钱是想看看我们家对你的态度,她只想让你幸福……”
一年后林西也当了妈妈,经历生育之痛养育之累,看着怀里无限依赖自己的女儿,她理解了素霞,开始想念素霞。
林西和素霞视频,发现妈妈眼角有泪,忙问妈妈怎么了。妈妈说,“没什么,我在参加你叔家妹妹婚礼,想起你结婚时候从家里走得匆忙,我没去现场,妈妈心里觉得亏欠你。”
婚礼现场,林西通过视频看到妈妈穿的是自己给她买的那身运动服,和婚宴的气氛格格不入。身边妆容精致的阿姨们都投来好奇的目光,问她怎么穿了运动服,妈妈骄傲的语气透过视频传过来,“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衣服。”
林西的眼泪落了下来。
曾以为最亏欠自己的人,实际上是自己最亏欠的人。
——————————
立夏之后
资若铭(26岁) 湖南省衡南县第二中学教师
立夏之后
绿意浓过一分,温度上升2℃
校园大道的树荫下
学生嘴角渐渐上扬
他们的笑脸,是世间美好的风景线
是单纯与繁杂的分界线
也是我日渐增高的发际线
五月阳光正好
用他们奔跑的脚步谱一支歌
歌名就叫青春
自导自演
背景已准备好,浓烈的夏天花红柳绿
正是孩子们喜欢的
还有,舞台,不必担心
他们呐喊一声
天地为之久低昂
至于,我
一直站在台下
笑着
没心没肺地笑着
微风吹过我手心
替我把每一次掌声
送给他们
——————————
碎花缝纫曲
秦雅洁(23岁) 安徽师范大学学生
衣柜里挂着一条深蓝底的白碎花吊带裙,那是我去年夏天快开学时买的。拿到手试穿后发现肩带长了些,胸腰也需要收一收。每遇到这种情况,我总会第一时间给外婆打电话。
我这习惯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家里几个碎花枕套,几乎每个都留着外婆打的烙印。这些枕套用了小二十年,虽然时间长了,但是胜在软和,加上没有大坏。但到底是时间久了,不时地总会冒出些小破洞,洞沿还有一丝丝的须。我还打趣过这个洞的情形和《红楼梦》里金雀裘破的样子不能说十分像,也有七八分相似了。神奇的事总会发生,每次让外婆缝过后再看,即使眼尖如妈妈,有时也找不出外婆把针脚都藏在了哪儿。
记得小学那会儿,学校要求每个同学套桌套。开学初老师挨个把桌套发到我们手里,至于是怎样发的、嘱咐怎么使用的、如何拿回家的,我是一概都忘记的,但记忆中却有一段画面非常清晰,便是外婆为我在桌套左下角缝名字和梅花。
阳台上外婆背着窗户坐在木凳上,下午四点多的阳光透过纱窗和玻璃,点点斑斑地靠在外婆肩头和臂膀,也洒入她膝上的浅蓝色桌套。她的手在针线筒里徘徊许久:丝线细,时间长了容易断;棉线结实,但写字可能硌着左手肘;红色醒目,但缝名字不吉利;蓝色呢,又和桌布颜色相同,不显色……外婆一手拿着鹅黄色线筒,一手拿着草绿色线筒摆在桌套前端详了许久。最后,她左手拿着针,右手捏着刚穿进的鹅黄色丝线,朝我微微扬了一扬,认真叮嘱一句“有断的就拿回来,外婆再给你缝”。小时候我是闲不住的,一边提着要小红花的要求,一边就想跑出门和大院的伙伴玩一圈。再回家时,桌套已叠成四折,整整齐齐地摆在茶几上了。折到最上面的那面,在我预料到的名字旁,没看到一朵小红花,却多出了一朵花瓣花蕊齐全的蜡梅。
小学毕业时,这个用了六年的桌套上添了一道又一道洗不掉的铅笔印、钢笔印,还有因为钢笔尖不小心碰在桌套上而氤氲开的一朵朵墨蓝色“小梅花”,它们或浅或深、或大或小,和左下角那朵还是很新的鹅黄色梅花相映成趣。这细细碎碎的花儿们聚成一团,总会唤起我更先前的那段记忆。
改好的裙子寄到学校,我试了试,全都刚刚好,又站在镜子前拍了照片发给外婆。“真洋气,我就讲一毫都没记错。”外婆是这么回我的。
看裙子上一朵朵连缀着的碎花,就好像在翻阅一本旧相簿。幼时外婆哄我睡觉时总要念叨,自己念书时功课门门都是5分,立志长大要当医生,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有念成大学,也自然没有当成医生。后来她自己学会了宽心,说当裁缝,也算靠手吃饭。再后来,外婆看到我上师范大学,就更加宽心了,“婆婆好像自己上了大学那样欢喜”。
那一朵朵细细小小的花承载着记忆与经历,陪伴外婆走过湖南、安徽各地。小碎花一个个串联起来,伴着缝纫机大连杆、针杆和钩梭上下联动发出的吱喳声响,那一帧帧影像,仿佛都在为外婆的人生造像,在诉说着外婆一生的同时,仿佛也在缓缓诉说这七十多年的时代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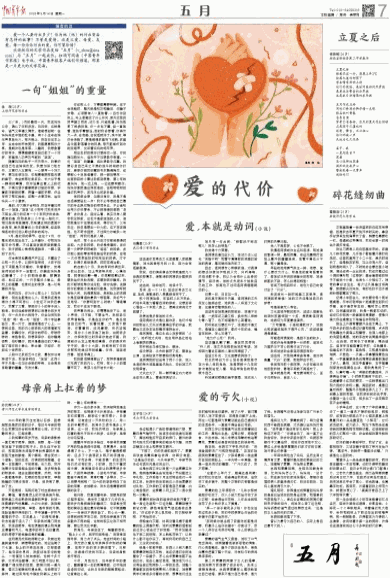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