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退休后常去文化宫里看人家跳舞唱歌,她尤其爱每月的14日,因为会有话剧表演。
我说,他们演来演去无非就是那几个经典的悲情本,演繁漪的阿姨估计都把泪哭干了。
姑姑说,除非她死,她泪才干。
后来,在一个14日,姑姑没有去文化宫,她说,演繁涟的人果真把泪哭干了。
那个阿姨姓连,年轻时从北方来此,听说本来是为看看远嫁的亲戚,没想到将心落在一个本地人身上,便再没有向北方回望了。
我想她是多爱她的丈夫。
连阿姨的丈夫是位剧作家,他们才相识的那会儿丈夫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就靠给三流杂志社投稿来维持生计。
连阿姨呢,是位永远心存梦想的“少女”。她听她丈夫说,他会用作品让她站上省剧院的舞台。
我听到此处连忙摇头,糊涂。
但没想到,丈夫的剧获了奖,要登台巡演,还有投资方想要拍成微电影。
连阿姨那时已经有了两个小孩,她从生活的柴米油盐里猛然抬头,去找她丈夫兑现诺言。
丈夫应允了,和一群所谓业内大佬并坐在观众席上,看连阿姨试戏。
她只有一句台词:“锁都找不到在哪儿?我怎么找钥匙?”
我觉得十分荒唐。
连阿姨也是如此认为,她没办法从这句“来路不明”和看不清情感的词里找到她的表演,毫无疑问她失败了。
自此,连阿姨专心照顾家庭,对表演的想法好像如乍现的火光,只听得响,然后消散干净。我以为会有什么出奇的情节,但没有。她的丈夫很本分地做自己的工作,却再也不过问连阿姨暗暗跳动的心。
日复一日,日日如一日。
在极其平常的冬天里,连阿姨的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她孤身一人后进了文化宫,这里有志趣相投的人。
姑姑形容她表演的那股劲,狠得不忍心看,一把年纪又跪又摔,换作别人早就七零八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架着她。
我听到此处要改口了,她爱的不是丈夫,是埋在心里的梦,像打十年的坐,锤百年的铁,怎么放得下。
“她为什么死?”我问。
姑姑瞳孔颤了颤,凑在我耳旁说:“听人说,她丈夫发病前给她打电话,她却因为看社区里的人演戏而漏接了。”
姑姑又补充,文化宫要被拆除了。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她总爱演那些尽在为他人泪的角色,她是想把十几年的梦与憾哭给世人看,用各样角色的悲去麻木自己。
听她虔诚赎罪的庙宇崩塌,她成无人打捞的失事沉船。
当人不再做梦,心也不会跳了。
我猜连阿姨或许全名叫连漪,和她演的繁漪一样,最后疯魔,命运如暴雨打在地上晕开的圈圈涟漪,她看不清也分不清,哪个圈是她。
年轻的她用勇气孤注一掷,她想,爱什么便成为什么。可是她的爱有些盲目了,像她试戏所说的词暗示的那样,她连锁都找不到,怎么找得到钥匙?
世间万物明码标价,她也为自己的爱付出了“代价”。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在思考,连阿姨到底爱谁?她的丈夫还是她自己的梦想?
可是答案无从考证。
文化宫被炸毁的那天,姑姑从话剧社的团长那里领到一个奖,是表彰连阿姨的,她被评为年度最佳演员。
“太可惜哩,小连知道就好了,她回头和家里说起来不得开心死。”姑姑话里满是遗憾。
可能连阿姨爱的,是回不去的故乡。
她或许当年是要争一份骄傲,但她也为固执与不甘心的爱付出了代价。
我问姑姑我会像连阿姨那样吗?
姑姑说,天地规律有舍有得,但如何衡量“代价”的度,那把秤在于我。
世间有无数个连阿姨,大多可能没有她那般执拗,意难平后就不再追究了。
爱本就是动词,肯定要消耗什么,至于如何标价,自在人心。
冯嘉美(20岁) 武汉晴川学院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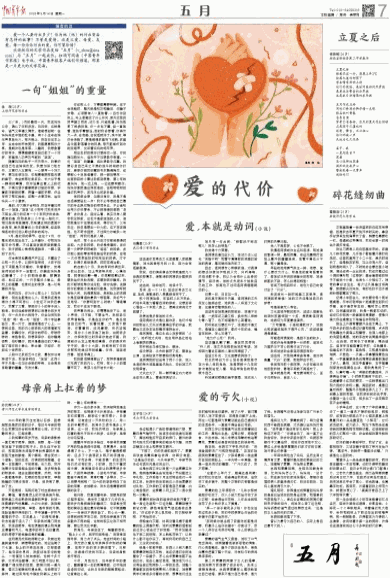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