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家,是承载爱的地方,是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共同的港湾。小家如此,大家也是如此,两岸三地,寰宇一家……关于家和家人,听听青年们讲述他们的故事。
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中国青年作家网,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家,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袁伟(27岁,苗族)江苏省江心沙农场有限公司职工
妻子临上学之前,总算吃上了一顿地道的家乡风味——干白菜炖排骨。在一碟糊辣椒蘸水的加持下,彼刻的她仿佛产生了一种要么确确实实身处老家,要么正在梦中酣睡的错觉。直到微信群里,传来母亲询问有没有收到快递的语音,才将她从离家1600多公里的现实中拉了回来。
正当我拿起筷子,准备品尝自己的手艺时,她突然伸出筷子挡开,说要先拍张照片发到群里展示成果。不一会儿,母亲发来一条语音,说菜看起来倒是不错,不知道味道如何。我放下筷子,精选了一个“美味”的表情包回复她。随后,弟弟也从离家1100多公里外的深圳,发来一张“点赞”的图片。微信群里的互动多了起来,没过多久,母亲又发来一个视频,父亲正在凉拌米皮。在红油与黄瓜丝的配合下,米香通过电磁波向我们发出共进晚餐的邀请。这时,妻子发了一个“流口水”的微信表情,而父亲也少有地参与群聊,回复了一个哈哈大笑……
在外求学的7年间,群聊已经成为我们一家人线上相聚的一种方式。父母在贵州老家的小县城里做小生意,弟弟在深圳求学,而我从扬州大学毕业后,又来到张謇的故乡海门,在一个国有农场从事农业工作。妻子刚研二,也在扬州求学。三五年内,我们一家人分散几地的局面依然很难改变。有时候我会在电话里感叹,什么时候才能一家人整整齐齐地聚在一起,永远也不分开。没想到,却被父亲说没出息:“老辈们常说,恋家的鸟儿飞不高,也飞不远。你年纪轻轻的,就该多出去闯荡闯荡,中国这么大,哪里不是家?我跟你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在外多年了……”
父亲的话,让我心生羞愧,脸也渐渐地发红、发烫。他说的都是事实,我不只一次听爷爷讲起父亲16岁就出远门打工的故事。但我的想法也没有错啊,自打我和弟弟被他们从老家接到身边上学,就开始了长达10年的“漂泊”生活。
初到广东,饮食和语言的天差地别,让我和弟弟觉得是一种煎熬。那时候,我们是彼此唯一的玩伴。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她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格外关照与关注。在她的爱护、鼓励和帮助下,我和弟弟才渐渐融入班集体,也慢慢学会了用粤语去交流。当然,成绩也比在老家的时候好了很多,父母仿佛从我们获得的一张张奖状上看到了他们不畏艰辛、流血流汗挣钱的意义。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父母因为工作环境和待遇问题,离开原来的工厂,在朋友的介绍下前往河南郑州的杜甫故里巩义市,下煤窑。
其实,对父母来说,他们是重回故地。早在18岁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在那个煤矿干过一段时间。后来结了婚,母亲觉得太危险,才不让他继续留在那里。从广州站到郑州站,人流汇聚成洪水,迅速吞没了我们昔日的一切美好、温馨的记忆。一张张疲惫、惊慌、空洞或怅然若失的面孔,让我对家产生了无限的渴望。当然,我所说的家,是一个固定的、永不搬迁的地方。
我和弟弟作为插班生,被分在两个不同的班级。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不同顺序的教材知识结构,我们都明白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事实证明,我和弟弟早已经具备了快速适应陌生环境的能力,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差不多已经可以用河南话跟同学和老师进行交流。一直到初中二年级,时间都是静谧流淌着的河水,没有波澜,只有安宁。但事实上,一场无声的告别,正在秘密的筹划中,并且不可避免地向我们走来——父母决定让我们再次转学,回老家念初三,然后考当地高中。办理手续的那天,我和班主任还有几个好伙伴相拥而泣,他们都理解这种无奈的分别,但却讲不出再见。就这样,用豫剧和烩面构成的“记忆之家”也迁出了那片金土地。
后来我跟弟弟如愿考上省内最好的几所高中之一,离家400多公里的住校时光,让我们提前体验了大学生活。家的味道,就是一周一次的电话粥,以及银行卡里的余额提醒。高考过后,弟弟去了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而我来了江苏扬州大学。
如今,我已经毕业并在一个国有农场打工两个月了。宿舍里安放下一些必要的家具后,空间所剩无几。公司领导多次让我更换大一点的宿舍,都被我婉言拒绝了。空间太大,就很容易放大孤独感,念家的情绪也就有了藏身之地。这些日子里,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在厨房里用油盐酱醋复刻家的味道,并重新构建一个家的概念。
时间越往后,我越理解父亲对我的“批评”,也更加明白了家的含义。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细细一想,无论是童年还是少年时光,我们的境遇莫不是这样。虽然都身处异地,背井离乡,但父母在的地方,就有用爱和责任搭起的一座庇护所。或许是一间瓦房,或许是一间职工宿舍,但不妨碍内心升腾起一份幸福和满足感。
在通讯极度便捷且多元化的今天,真可谓应了王勃那句“天涯若比邻”。在以“自己人”三个字命名的家庭微信群里,我们构建起一个可移动、可视化的家。大事小事、生活点滴都可以随时随地分享。父亲的话,同时也让我深入思考家在新媒体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新书写方式。在爱与被爱、关心与被关心、理解与被理解的隐性情感互动中,每个人都是构成“家”的笔画,相互间不同的距离,不一样的生活轨迹,不一样的习惯,让这个字看起来更丰满,更具有时代气息与精神指向性。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潘美辰歌中所唱的家,我已经拥有了,它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让我牵挂,也给我不一样的温暖和寄托。
——————————
归家(小说)
冯嘉美(21岁)武汉晴川学院学生
再回到畹町(中缅边境城市——编者注)那天万里无云,天湛蓝如水洗过一般。
因为疲于回答村寨中人们的问题,我溜出家门,驾驶汽车上了滇缅公路,一路朝前开去,仿佛这样可以甩掉现实里的细碎鸡毛。
直到山头吞没了最后的红光,天色逐渐深重。我想调头,却发现冷却系统警告亮起了红灯。
靠边停车后又发现手机没有缴费停机了,想伸手拦车,几次尝试都无果,最后选择原路返回寻找服务区。
一小时后,我来到一处桥梁附近,借着朦胧月光,我看清楚桥头的刻字——惠通桥。
天色越来越黑,前方的路昏暗到不得不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时我猛然反应过来,应是走下了公路。
小路的泥泞,过耳的凉风,以及不知名的虫鸣。我内心直呼不好,慌乱之下,脚底打滑,往前摔去。
“小心!”有人拉住了我。
“小姐,你是迷路了吗?”
我随口敷衍过去想要离开,紧接着他又说:“你现在的方向是往山下的河流去。”
我顿住脚步,迟疑起来。“我可以带你出去。”我不作声,脑海中闪过无数种求生措施。“如果你心有疑虑……”他捡起一根树枝,“你可以牵着那头,我拉这头。我走前你走后。”
我愣住了,小心把手机往上抬了抬,看清了对方的样貌。他眉眼有神,轮廓清朗,上身一件白色竖条纹衬衣,下身一条墨绿色工装裤,款式区别于市面上的热销款。
正犹豫着,头顶忽然有鸟夺枝飞出,心惊胆战下我选择抓住了那根木棍。
他按他答应那般,带我一步一步往前走。
掠过安静的氛围,他主动打破僵局,“你是外地人吗?”
“不是,我只是在很小时出去念书,今天回家看看。”
他沉默了几秒后,用感叹的语气说:“回家看看,挺好。”
“那你呢?”“我……我是外地人,老家广州。”“你没有那边的口音。”“我也是小时候出去念书的。”
……
在对话中我了解到,他是名工程师,受一位陈先生的邀请从马来西亚来这里工作,住在道奇宾馆。
他的谈吐合宜,又不失幽默,这使得我紧绷的神经得以放下,不知不觉间我和他又重新回到车辆停靠的位置。
他上前帮我检查,眼中闪过几丝诧异。
我有些担忧:“是修不好了吗?”
“没事,这些车的构造应该大差不差。”
他中途花费许多时间取回来了河水。“加普通水容易生锈,堵塞水箱。但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让发动机冷却了。”他边解释边操作着。
果然,车子又能发动了。
已是深夜,他好像看出我的顾虑,说:“我可以陪你等到天明。”
我们坐在车内,顶着暖黄色的灯光畅聊着。
他明明很年轻,但是总有种历经世事后的稳重感。他问我在哪里读书,我说先是去了昆明,后来考去北京,接着申请到互换生资格去了英国。
他问:“北京是首都吗?”我很疑惑,说,是。“那你从这个地方出去……”
我立马接上他的话,“我的父亲是位性格潇洒果断的人,改革开放后他借钱出去做生意,所以家中条件不差。”
他点点头,不知怎么,他听到这些好像很开心。
“外面是什么样的?”
我从儿时记忆里的少年宫科技馆说起,再到去北京以后见到的名胜古迹,还有英国的唐人街。
听到此处他突然正襟危坐起来,问:“你在国外有没有被欺负,或者遇到危险?”
我笑道:“怎么会,现在社会环境安定许多,而且我是中国人。”看着他的眼,我说:“如果在外遇险遇灾,避难场所上空第一架飞来的飞机,永远是中国的。”话音落地,我好似捕捉到他湿润的眼。
就这样,话题最后落到他想念的家乡美食上,而窗外的天也逐渐亮起来。
他主动下了车,告诉我快回家去,家里人心中一定着急。
我笑道:“他们都习惯我常往外跑,兴许我现在回去他们还在睡觉呢。”
“一定有人等你回家的,快走吧。”他说时,有些催促。
轮胎摩擦过石子发出粗糙的响声,隔着下降的灰尘,我看向他,那蒙蒙亮的天只有几束光落在他的肩头,我想到什么,说:“能问你的名字吗?”
“我叫林嘉祈。嘉峪关的嘉,祈福的祈。”
“我叫蒋华菱,取自楚辞‘芙蓉盖而菱华车兮,紫贝阙而玉堂’。”
他点点头。
“等去广州,我请你吃肠粉!”我留给他一句话,便往家回。
没想到的是,这次阿妈竟坐在院子里等我,她怕我玩回来肚子饿,早早备好了饭菜。我不禁自责,坐下狼吞虎咽起来。忽然我又想起林嘉祈,我和阿妈说,我遇到一位好心的工程师,他帮我修车。
阿妈却反问我:“怎么会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工程师到这里呢?附近都没有村镇要修建什么,而且工程师来都住分配的宿舍,怎么会出现在……”
我听后,有种后知后觉的凉意。
我放下碗筷再次冲出家门,借表哥的车子再开回原来的地方,林嘉祈早已不在,我四处寻找,脑海中浮现着当时与他相处时的那些异常。
惠通桥。
这次,我仔仔细细看过了惠通桥,我便是从这里开始迷进那段曲折的路。
记忆不断交织,勾勒着那位名叫林嘉祈的人,他有些良好的教育背景,总把北京说为北平,他有年轻俊朗的容颜,却有满是老茧和伤疤的手。他说他来工作,是工程师,还是司机和修理工。
我打趣他,小青年,你为什么穿着老过时的衣裳。
一切都在他的笑而不作声中有了答案。
在畹町,有一座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里面纪念着的是被陈嘉庚先生号召回来的3200余名南洋华侨青年志愿者。他们此次回家,是为了救国。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交通逐个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物资运输通道。
在馆内满墙的黑白照片中,我找到了林嘉祈。
他出生于1914年,年幼时就随家人移居马来西亚,其间没回过国,直到1938年他留下家书告别亲友,这才有了他的北归。这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林嘉祈最终死在惠通桥上。惠通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也是日军重点轰炸的对象。林嘉祈他们的任务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轰炸中,把惠通桥一次又一次地修建好。
馆内,他亲手写下的家书还被保留着。信上说:“别了,家园处于危难边缘,是我这只大雁归家时。”
不经意间,我注意到在他家书下面还遗存一张他日记的残页。上面的字迹略微潦草,我竟在其中依稀分辨出两个字:
华菱。
“1939年8月1日晚,成功运输完我所负责的物资后睡下,梦中我在惠通桥附近遇见一位女士,她着实奇怪还有着非凡的经历。我爱同她交谈,因为在她的话语中,未来的祖国站起来了。我相信她所言非假,我永远相信中国人不会倒下!我也会一直记住她,华菱,待到和平之时再重逢!”
读罢,不知何时已泪流满面。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我相信我们也会再重逢,无论以何种方式。
因为先生,你已归家,而我便在这里。
——————————
我们是一家(童话)
姜士冬(23岁)长春师范大学学生
天气晴朗,鼠小弟坐在自家的院子里堆积木。一块一块的小积木,被鼠小弟一番拼凑后,就拼成了一座积木城堡。
百灵鸟姐姐刚从很远的一座岛上飞回来,她瞧见了这座积木城堡,不由地赞叹道:“哇,真好看呀!鼠小弟,你可以借给我一些积木吗?我也想拼城堡。”
“一些积木呀,那可借不了,要借就全部借给你。积木城堡,缺了任何一块积木都不行哦。”鼠小弟缓缓说道,“就像有些字,缺了任何偏旁部首,甚至一笔一画,都不再是原来的字了,也像一个国家,缺少任何一座岛屿都是不行的。”
把积木全部借给百灵鸟姐姐后,鼠小弟便离开家,去外面玩了。
鼠小弟走在路旁,看到了一棵孤零零的小树,便问道:“小树小树,你有名字吗?”
微风吹拂,小树微微晃动:“我有名字,我叫‘木木’。”
鼠小弟又走了一会儿,看到了两棵小树,便问道:“小树小树,你们有名字吗?”
两棵小树呵呵笑:“我们有名字,我们叫‘林林’。”
鼠小弟走到路的尽头的时候,看到了三棵小树,便问道:“小树小树,你们也有名字吗?”
三棵小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起笑着回答:“我们有名字,我们叫‘森森’。”
鼠小弟这下可蒙了,挠挠头,心想:“小树们竟然有这么多名字呀!”
“那如果是三百棵树、五百棵树呢,那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呀?”鼠小弟好奇地问道。
“他们呀,通通叫‘森林’呀!”
“一人不成众,独木不成林。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远远的歌谣声传了过来,鼠小弟听到了,顺着歌谣声寻过来。
原来是三只小猪在拱地,一边拱地一边哼唱着歌谣嘞!
“小猪哥哥们好呀!”鼠小弟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三只小猪也打着招呼:“鼠小弟好呀!”
“哇,你们三个这么团结呀,都没有偷懒的。”鼠小弟竖起了大拇哥。
“二人从,三人众,三只小猪的力量更大呀!”
跟三只小猪拜别后,鼠小弟又去拜访了松鼠妹妹、豹子奶奶和河马爷爷。鼠小弟从日头正足的时候出去溜达,直到月牙挂在夜空中,才回到了家。
“哎呀,可真是从‘日’走到了‘月’,明天我还要出去溜达。”鼠小弟一拍脑门,“哎呀,‘日’加‘月’不就是‘明’了嘛!”
鼠小弟躺在柔软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鼠小弟自言自语:“两个‘木’加在一起就是‘林’,三个‘木’就是‘森’了。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从’,三个‘人’的话,就是‘众’了。‘日’加‘月’就是‘明’,那‘不’加‘正’就是‘歪’。还有这个字,这个字,都能凑成新的字。”
就在拼凑第二十二个新字的时候,鼠小弟沉入了甜甜的梦乡。在梦里,鼠小弟坐在自家的院子里堆积木呢,不过每个积木上都是一个偏旁或部首,或者是一个字。鼠小弟将这些积木都很好地组合在一起,都让它们成了新的字。
在梦里,鼠小弟还看到远远的小岛上,百灵鸟姐姐也在堆积木呢。鼠小弟笑呵呵地说:“此岸加彼岸,才是一家人。”
“我会把你们都组合起来的,因为我们是一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呀!”鼠小弟对着梦境里的积木说。
——————————
家和父母
刘登发(25岁)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生
说来也荒谬!本该最关心自己婚姻的子女往往是最无动于衷的,而父母则往往是最心急如焚的。
到了该结婚的年纪,父母的每一声催促仿佛都是在宣告我们的青春已到迟暮。而作为子女的我们似乎执拗地不肯承认这一现实,对于相亲、催婚竟是那般抵触,仿佛婚姻是自由的桎梏,而家庭则是人生的坟墓。细细品来,子女的挣扎还颇有些如杨花般“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的悲壮!
每一次回家,最尴尬的莫过于父母询问是否交了女朋友,最讨厌的是总有些客人会再提醒一次,我不免再一次“嗯呀”“啊呀”地搪塞过去。我恨不得把这些狗拿耗子的人摁在地上,挽起袖子,抡圆了臂膀,一巴掌紧跟着一巴掌扇在他们脸上,嘴里还得嚷着:“叫你多管闲事!叫你多管闲事!”
有一次,父母讲起了二伯公的家事(伯公是我们这里对于族中和父亲同辈而年纪长于父亲的长辈的称呼):二伯母以前非常凶悍,经常和老二伯公闹矛盾。有一天,老二伯公带着些糖果来到我家,是带给我吃的。老二伯公很疼我,只不过那时我年纪小,不记得了。那天他嘴里还念叨着,以后就见不到我了。老二伯公回家以后就自杀了。说到这时,我父亲总是叹息:我爷爷脑子不灵光,没反应过来,那时只有我和爷爷在家,要是我爷爷反应过来,老二伯公就不会死了。
初次听到这个故事,我有点惊奇,这种好像只有小说、影视剧里才能看到的片段竟然曾经发生在我身边。同时我也很感动,一个我没有丝毫印象的老人竟然那么疼爱我,临死之前,居然想着带糖果来看看我。但我心里最多的还是疑惑:既然二伯母逼死了老二伯公——二伯公的父亲,那么不论谁是谁非,二伯公和二伯母怎么可能安安稳稳、和和睦睦地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呢?我不记得父亲说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说的话没能回答我的疑惑。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天,我的父母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纠缠着他们——老二伯公的悲剧会不会有一天也降临在他们身上?等他们想到寒入骨髓、头皮发麻的时候,又忍不住在心底暗暗责骂自己,怎么会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呢?他们也深知悲剧再现的可能微乎其微,但这微小的可能也足以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夜晚折磨得他们难以入睡。
当子女走进婚姻的殿堂,组建了新的家庭,也许牺牲最大的就是父母了。自己照顾了大半辈子的孩子,从此和一个与他们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贴心贴肺,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新旧两个家庭之间,使得他们和孩子的关系显得那么疏远。他们也许会急迫地想要靠近一点,却只能被这堵无形的墙无情地挡在另外一头。但就是这样,他们依旧愿意为子女的婚姻操心。就算子女埋怨他们絮叨、聒噪,他们仍旧无怨无悔!
他们本不必为此操心,他们的晚年已经有子女陪伴他们,照顾他们了。他们只是希望,当自己的孩子也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连拄着拐走路也颤颤巍巍了,也能有家人代替他们互相照顾,代替他们陪伴着自己最疼爱的孩子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作为子女的我们,常常自诩为具有现代意识的进步青年,而将父母视为思想保守落后的、终将被时代所抛弃的人。我们将婚姻和家庭看作是对我们个人权利和人身自由的侵犯与压迫,而父母则是尚未觉醒的、只知道机械地完成不同阶段人生任务的机器。实际上,也许我们才是那个肤浅的人,从未充分地、客观且全面地权衡过得失利弊的人,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的人。
父母,以其朴素的直觉和经验,往往做出最明智的抉择,才是对家庭和人生的本质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每一次我们对父母斗争的胜利,很可能都是父母出于爱护而做出的妥协与纵容。我更愿意以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去衡量,而不忍心以冷冰冰的想法去揣度每一个父母的任何并不过分的行为。我们可以有更聪明的做法去妥善处理与父母的冲突。
家庭是爱的赞歌,而婚姻是家庭的序曲。愿我们以谨慎且负责的态度去谱写人生的乐章,而非以憎恶的态度将琴弦绞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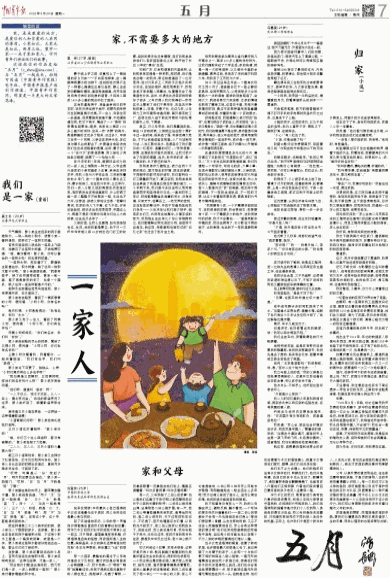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