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铁路破秦岭而入,南北贯通。故乡关中和陕南相通,依山势而修建,伴溪水蜿蜒曲行。多年前高考完后因赋闲便考得驾照,后远赴他乡求学,无暇练车,此项“技能”遂被搁置。如今,去往他乡不得不乘火车、高铁,一来二去虽费时疲倦,却也乐意无穷。
烟雨袅袅,微风徐徐,秦岭山常邂逅漫漫细雨,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似一幅自然、清淡的水墨画,缓缓铺开。火车疾驰越秦岭而过,穿洞而行,时隐时现,冷暖交替。我稳稳地端坐在车厢,入洞时周围黑压压的一片与出洞时豁亮亮的四周形成鲜明的对比。
汉江之美,人们总说美在汉水。白河县,坐落在陕西安康市的东部,北邻汉江,隔江与湖北相望。白河县火车站就隐蔽在崇山峻岭间,似一隐者,醉卧在落花处,四方游人慕名而来,见山见水,乐哉乐哉。我就是游人中的一名,从小生长在关中平原,未曾见到过这秀丽高峻的山脉,只想这山于安康、白河只是一角,没想到这山竟气度非凡,包囊座座楼房、户户人家。出租车载着我在大桥上飞驰,桥下潺潺汉水奔流不息,悠然的流水、浅绿的水色、如绢的波光都是我从未见到过的。
阿姨就在县中小村等待着我,这里山高坡陡,绿树成荫。我生怕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就试着说了句话:“阿姨,空气真好。”“穷山恶水,没有你们那里的平地好。”她的话,我听得七分,其余三分倒也猜得着。紧随阿姨一路向前,山中人家住得零散,山顶、半山腰、山底都三三两两有些住户,他们成一群体,相互照料。房大多三层,白瓷锃亮。一月之前的傍晚,阿姨打来电话说爷爷生病了,走访白河和武汉大小医院,均不见好转,家人在“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中几经犯难。因爷爷年龄偏大的缘故,综合评估之后选择了“保守治疗”,止痛药、营养药隔一段时间就要注射,以求延缓病痛。
去往山上爷爷家,有一处自然景观,夹在两山之间,沟壑纵横,瀑布飞流。叔叔说:“山中之水天上来,那都是真正的山泉水。”弯路顺延向上,只能通行一人,上去后,四周仍被群山环绕,倒也有几处平地。幽静的山中,传来哗哗流水声;前山后山错着节奏,不时有物打着快板,清脆悦耳,响彻山林。正疑惑着,叔叔解释说:“啄木鸟的尖嘴击打着树洞,正医治树洞。”
爷爷虽久病缠身,体力欠缺,听闻我来,还是扶着墙赶来迎接。他与奶奶栽种蔬菜、挖笋砍柴,房虽破旧斑驳,也舒坦自在。屋前有一棵樱桃树,轻薄、重重叠叠的绿叶之间,缀满了一颗颗如同玛瑙般晶莹剔透的果实。爷爷轻声慢语道:“摘些红樱桃吃,粉扑扑的要再过一天就熟透了。”树瘦高,樱桃也显小,我们用竹竿制成弯钩,蛮力拉住树枝,往竹篓中摘取,不过一会儿,樱桃便溢满了小竹篓。
临近傍晚,我与爷爷、奶奶拥抱告别,劝他们及早回屋休息,转身泪水湿满眼眶。爷爷中午只喝了几口汤,因为他的胃部已溃烂;奶奶只含下几块嫩豆腐,因为她的牙早已掉光。我不舍与他们告别,又不忍看见他们常常饱受痛苦,想到这里,我竟加快脚步往山下走了去。
曾与叔叔聊起爷爷,他说:“生老病死,都是宿命。”沉默许久,我说:“尽力就好。”在安康,在白河,真正意义上我只待了一天。返回故乡时,我又一次乘坐火车穿行秦岭,与来时一样,秦岭山洞中的火车时隐时现,忽明忽暗,像极了我们的一生,总有欢乐喜悦、痛苦悲伤相互交织,相伴而行。途中我不间断地叩问自己,什么是远行?于我来说,见所见山,见所见水,见所见人,皆是远行。
人,应该如同山一样活着。
俱新超(2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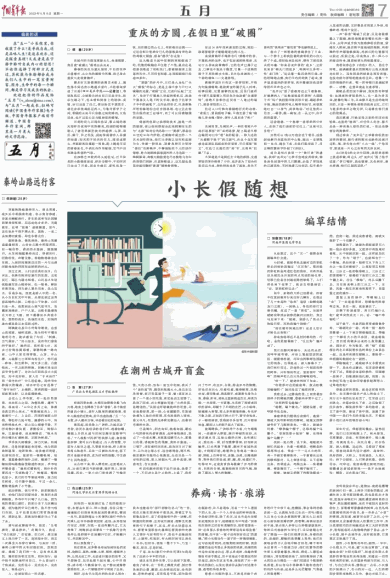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