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方圆里周旋太久,每逢假期,我总爱“破圈儿”般地出去走走。
暮春的风在为夏天预热,午后的世界正透着光,从公车的播报中苏醒,我已身在重庆九龙坡黄桷坪。
踏步在五彩错落的涂鸦艺术街上,随性拣不知名的小路漫步前行,不经意间穿进了川美(四川美术学院——记者注),等到发现后,立刻努力扮出自己还是学生。技法生疏之下,也未曾料到身上的胡须、皮鞋,早已出卖了自己。事后发觉不禁莞尔,被社会洪流淘洗过的人,与象牙塔学子之间,相隔的从来不只形貌之间的鸿沟,大抵说来,也不过是心灵与眼神里的褶皱。
川美的花儿开得有些早,像山城的春天那样在夜雨中突然醒来。校园的植物圈陷入了被花草疯狂统治的趋势,头顶、身后、脚下,目之所及,到处伸展着待人采撷的绿意;知名和不知名的花儿,埋首或探头,齐刷刷各自撑起一枝春。配上随处可见的青春面孔,不消光合作用嫁接,空气中自有满是希望的气息。
在涂鸦艺术街的尽头处驻足,打不知名的小路继续前进,碎步交错中,不知何时已走出了川美。闲坐半刻后,索性纵身一跃,站在路边的山石上,向前极目远眺——过往在相片里神交已久的那极具传奇色彩的两根大烟囱,原来“潜伏”在这里!
这大概是主城中仅剩的两根烟囱了吧,饥饿的眼睛忍不住看了个饱,最后还是把景色喂进了相机快门。看着烟囱顶上蓝蓝的天空,不用问也知道,这两根烟囱已经退休多年。
“冒烟”的岁月中,它们是九龙电厂生火“做饭”的标志,更是主城千家万户灯火阑珊的光源。“戒烟”之后,它改行玩起了“文艺”,站定于行摄旅人举起的相机后,流淌于墨客文人笔下的文字间,着色于名家学子手中的画笔下,以作品的形式,代表黄桷坪的形象地标出征全国各地,也让正在转型升级的前工业城市,有了可以回溯触摸的证据。
烟囱的色彩让我想到美术,画笔一样的烟囱,更让我回想起由此地脱颖而生的与“北漂”相对应的名称——“黄漂”。那是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在黄桷坪诞生的一个艺术创作群体,他们大多数以创作和卖画为生,凭着一腔热血,顶着各种压力坚持“漂泊”在黄桷坪,不懈地皈依个人的创作理想,努力地细描画里画外的人生色彩……细细算来,两根大烟囱竟也巧合般地与当年的首倡们同龄,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也是现存最完整的“黄漂”精神参照物。
而这30余年传承演变的过程,宛如一段需要配茶才能缓缓道出的人生。
来到黄桷坪不喝茶怎行?黄桷坪的茶,不像杭州的龙井,也不似安溪的铁观音,无论什么茶来到黄桷坪,它的名声已属于过去,口碑也不取决于籍贯,它像一个成熟的游子不再依赖出生地,名字也将被附上一个新的载体——交通茶馆。
黄桷坪或许只有这一家茶馆吧,不然为何装潢精致、地段黄金的铺子无人问津;招牌旧陋、位置偏僻的此地,反而门庭若市?要不是墙壁上用旧色字体涂着“交通茶馆”,我绝不会相信这仅容一人通过的偏门,便是茶馆的入口。
但这入口仿佛有着隔绝时光的功效:“老板儿,紧到捱啥子嘛,不做生意了唛?端碗儿茶来噻!等哈,茶叶儿莫抖多了哟!”
……
未闻其茶,先闻其声,一种在老照片中或旧故事里“听”来的场景,配上眼前不修边幅的对白中“看”来的配音,一种久违的“光着膀子就干”的江湖气,在这个连瓦都感觉是胡乱码起来的弄堂里,平日那套“斯文”,在此口无遮拦的“闹”市,无需再“狂飙”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网红打卡地的原因,交通茶馆的茶价格贵了少许,也许是为了迎合有朋自远方来,茶的种类也多了起来,原先不曾有的“铁观音”“菊花茶”等也赫然纸上。
我点了一杯普通的盖碗茶坐了下来,与一个脖子上和我挂着同款相机的小伙儿拼了个桌。得知他来自杭州,便有了胡侃谈天的兴趣:“你来自龙井茶的‘故乡’,正好我来自‘朝天门的故乡’,咱俩可以多吹一吹‘龙门阵’。”这话像一根活络的引线,将他的情绪点燃,我们不约而同笑了起来,笑声溢进温热的茶杯里,再扑腾着回流进茶馆的市井声色之中。
“龙井兄”望了望着旁边正下着象棋、打着牌的人:“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大隐隐于市’吗?”我回望四座沉思片刻,端起茶杯半抿,微淡的香苦味入喉带有回甘,再悠悠地吐出一口茶气,淡淡地说:“对这里的人而言,一碗茶,跟一碗饭,在一天之中,似乎同样重要。”
话音刚落,一个抱着一沓厚纸的中年人,走到了我们桌前的空位上:“这里可以坐吧?”
当然可以!我以为他会坐下看书,没想到他解开灰蓝色的中山服,掏出一支钢笔和一本书,端坐下来,在我们眼皮底下,用正楷的繁体字抄起了《诗经》。
或许是怕打扰到一个“修行者”的虔诚,我和“龙井兄”心照不宣地没再续谈,倒是房柱间笼中的几只鹦鹉,沾染了茶馆里的江湖风性,不时地凑几句闲话,似乎想介入某桌的话题,又好像是在同某人争执,张嘴碎语,喳闹个没完。
一声“添茶”喝破了沉寂,只见老板娘戴上了眼镜,熟稔地端着壶嘴长长的一罐开水,以呼声或手势为指路牌和目的地,穿梭在人群间。她仿佛不受地域的限制,再细微的呼声都能够捕捉,再挤仄的位置都可以到达。所到之处,自成焦点,有一阵小小的闹动传来,随即被更大的喧嚣湮没。
我看向旁边抄《诗经》的人,他左手持笔,浸满碳素墨水的钢笔行云流水地游走在纸上,没有因我的刻意注视而放缓,也没有因为茶馆的插曲而注目。他像一个目的明确的行者,唯一的停顿只是端起茶杯……对啊,这里毕竟是交通茶馆。
默默品茗的某个瞬间,我突然有种错觉:这满座的茶馆里的人,无一是为茶而来。就像吃喝二字,从来都不是生活的最终目的,只是一种惯性使然的肌肉记忆。它们与更多的身外之物无异,只是填充我们身心的附属品。
我沉默着,开始觉得之前的用词有些轻率。这里的“喧闹”,对任何人而言,都不会是一种具备入侵性的打扰,一如这动静皆宜的黄桷坪。
回过神来,“龙井兄”正举着相机抓拍添茶的瞬间,修行者的眼光也始终没离开过纸、笔、茶勾连出的“三点一线”,于他而言,那或是一片心之所向的无形区间。
从《诗经》的文字中回眸,我把茶盖朝上放进茶碗,转过头,对“龙井兄”扬了扬手说道:“茶已喝好,我也歇够,天色将尽,春亦将满,咱们江湖再见吧!”
谭鑫(2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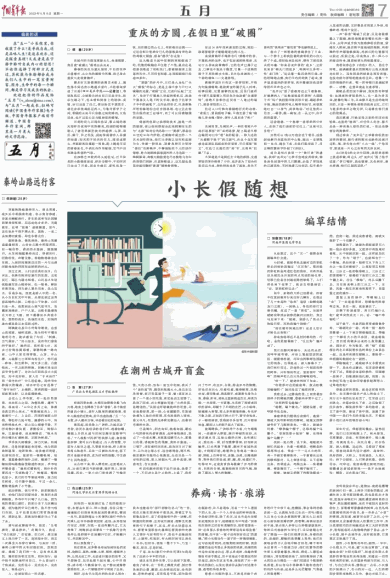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