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人生总是充满意外,比如生离死别。对一个人最深的思念,会在某一个瞬间淹没一切。但我们更应该学会接纳和坦然面对,因为,你更好地前行,才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中国青年作家网,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思念者
冯嘉美(21岁)
刀秀群在还是个少女时就嫁人了。
她从一座大山来到另一座大山,长途跋涉中与丈夫的相互扶持算是新婚的赠礼。
丈夫比她大8岁,在她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并留下3个孩子。
刀秀群嫁过来后,日子继续不咸不淡地驶向前方。
她偶尔会站在山头遥望,试图从相似的绿海中窥探出什么。
某天,遇大雨,泥屋受潮后更阴冷。丈夫是沉默寡言的男子,他只会用臂膀环抱住她,忍着,忍着,直到天明。
刀秀群听着噼里啪啦的雨点开始明白,她有了不得了的情感,叫做思念。
思念是一种暴力的情感,极其容易闯入心房,而后开始胡乱碰撞,直到留下满目狼藉。
不过,庆幸的是,刀秀群是个平和内敛的女人。她鲜少展示情绪波澜,笑也是微微的,烦也是微微的,好似万事万物都不配令她侧目。
所以即便思念肆虐,刀秀群仍然可以接过每一招。
刀秀群的丈夫是名赤脚医生,每每出门,需要用许久的不相见为代价。
离开前,丈夫常会问,要带什么。刀秀群细细碎碎说过一大堆后,总会附上句,回来就好。
丈夫点头,然后便走,刀秀群则转身,继续留在老屋下。
她带着孩子,守在老破的瓦房里,捱着情感从背脊划过的岁月。
后来她又为家里添了5个孩子,狭小土地上围满以她为圆心散开的血脉。
刀秀群开始倾斜重心,将自己专注在儿女身上,以为这样她的思念可以不再漂泊。
可惜刀秀群失策了。
丈夫被地主叫去打牌,这是场永远没有公平的赌局。丈夫赢了,能回家;输了,要跪着,双手合十后再被绑起来,从中间插一根削尖的木棍,忍着痛继续打,打到地主觉得他赢了。
刀秀群不言不怒,她知道动情绪没用,但她擅长习惯,习惯一切向她冲来的东西。
丈夫有天没有回家,病倒在某条山路上。他医治许多人,却没救过自己,糜烂的双手要对外宣称,是摘草药留下的痛。
刀秀群带着孩子,安葬了丈夫,她的思念,死去了一个。
家,总要有人去支撑。
丈夫与前妻生的老大老二长大了,他们背上行囊,走出大山。
刀秀群像送丈夫般,送别他们,话语结尾附上回来就好,然后转身,继续留在老屋下。
她的思念又漂泊起来,还好她擅长习惯。
日子是瞎眼的犬,不顾地向前。突然有一天,撞上什么东西,吓人一跳。
刀秀群的老七死了。因为肚子饿,去逮蜘蛛,火烧了吃下。
刀秀群还是那副平淡模样,带着其余孩子埋葬老七后,又重新回到生活的轨道。
慢慢地,其他儿女也长大了。
刀秀群计划着,隔几年送出去一个,再隔几年再送出去一个。
可惜,计划最没有诚信。
刀秀群的老四去了城市,老五也跟着去了,等老五回来,她说她动心隔壁城镇的男人,她嫁走了。再后来,老五回来拽走了老六。隔年,没考上大学的老幺也跟上脚步。
待刀秀群反应过来,转身看,家里只剩下好吃懒做的老三。
她很淡然,继续过着生活,与从前无差。
新年,儿女会从四面八方回来。老屋会热闹一阵。
刀秀群依旧那副样子,对什么事仅是抬眼,看看,点头便带过去的态度。
日子形成一个轮回,刀秀群站在其间,不管不问,接受种种相似的瞬间同她擦肩。
她擅长习惯,围满土地的人散开又聚拢,对她而言仅是固定行踪的运动。
新日子,政府下发补助,帮忙修建了新房子,刀秀群得以摆脱委身于老屋的生活,儿女也在周边盖了新家,不过只是盖着,人还在他城。
刀秀群知道,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还好,她擅长习惯。
我有时候会想,刀秀群能习惯多久。她活了八十多年,习惯了八十多年。
直到去年,她突然不再习惯了。刀秀群开始变得情绪多变,容易哭容易闹,容易离开家,容易无助地停在某处陌生的地方。
她记不起周遭的一切,所以习惯的本领也自动解除。
儿女都回来了,围在身边。
刀秀群想不起他们是谁,她重新望向远处的绿海,即便那里什么也没有了。
我也回来了。
妈妈说,多跟外婆讲讲话,万一她记起你来。
我尝试和外婆说自己的名字,她先是疑惑地看着我,再是抗拒,而后又是小心尝试,最后颤抖着唇,试图发音。
而我在发现她眼里闪过一丝哀愁时,打断了她的回忆。
不记得最好。
这是神对她受思念胁迫了一生后,给予的恩赐。
外婆走时很安详,也算圆满。
夏季,山雨细碎连绵,打在排成一条的队伍上。男人女人低着头,嘴里唱着我们民族的歌谣。
那些空灵又陌生的音符从山头连到山尾,送完外婆最后的旅程。
墓碑安下,同人们对立。
大家低着头,从此,该承担思念的另有其人。
反正,再也不会是刀秀群了。
——————————
第二次再见(科幻小说)
王孜轩(21岁) 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
地震
地震发生在凌晨,刹那间,天旋地转,山崩地裂。王梓从自己的数据研究公司走出来时,弥漫的黄土与灰尘已经将天空遮蔽。几缕凄冷的星光透过大气打下来,为王梓与市区同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纱。
一滴水点到了王梓的鼻头,紧接着是两滴、三滴……王梓抬头看去,发现无数雨滴正从天而降。地震未平又遭暴雨,这对城市的救灾情况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突然,连接机密存储室的报警器响起。他心中一紧,向着公司全力跑去。
机密存储室的门是敞开的。王梓的心被揪了起来,他穿过大门进入内部空间,并在看清眼前的景象后跌坐在地上。
机密储存室空无一物,他的母亲被人偷走了。
暴雨
“杜先生,求求你,这台微型超算集群是我最重要的物品……”
临时搭建的救灾指挥棚中,王梓紧紧地握着管理员杜钥的手恳求对方的帮助。但杜钥只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对,算力严重不足。我们在尝试远程操作计算机集群进行数据处理,但仅靠卫星传输很难实现。什么?数据中心突然出现了……”
还未走远的杜钥接了一通电话,可王梓并未听到,只是呆呆地望着远处。
暴雨洗刷着这座刚刚遭受创伤的城市,僵在原地的王梓也同他脚下的土地一样,因超算的失窃多出了无数道裂痕。
如果母亲此刻就站在他的身旁,那她一定会伸出双臂拥抱自己,即使全息投影很可能会穿过自己真实的身躯,王梓想。
母亲啊母亲,你在哪里?
废墟
不顾他人的劝阻,王梓来到了一片老旧小区的废墟附近。破碎的水泥叠在一起,一节断根的绿色爬山虎躺在裂缝中。废墟旁学校的操场上撑着帐篷,帐篷在风雨中飘摇,奔走与呼喊声时不时顺着风传出,落入王梓的耳朵。
王梓走到废墟旁,捡起一片玻璃。他想辨别出哪些碎片属于自己曾经的家,可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手中的瓦片,王梓感觉自己仿佛又走进了老房屋中,遇到了年轻时的母亲。
小时候,身为公职人员的母亲很少陪伴在王梓身边。但那时的王梓并不怨恨母亲,恰恰相反,他以有这样尽职尽责的母亲而自豪。
转折始于父亲的病重。父亲患上肝癌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为了让父亲好起来,王梓想尽了办法,他甚至悄悄地向流星许愿将病痛转移到自己身上。可即便他许下了这样的愿望,父亲手背上的肉还是一天天减少,最终塌作包着骨头的一层皮囊。
父亲病危那天,大雨倾盆。在家中写作业的王梓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她说自己现在去接王梓见父亲最后一面。于是王梓在一行又一行的眼泪中飞快地换好了衣服,随后站在自家窗前等着母亲的汽车驶入小区。
然而,任凭王梓将漆黑如墨的天空望成微微亮光的黎明,母亲的汽车也没有出现。后来他才得知,母亲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交通事故,她停下车子救出了被压在车下的两名男子,却也因此错过了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父亲去世后,王梓几乎断绝了与母亲除必要交流外的一切交谈。有时候他能感觉到母亲眼中的愧疚与对他的关切,但她依然很忙。
高考前一天晚上,王梓翻开小时候的梦想册,将“成为像母亲一样伟大的人”划掉,写上了“离开这座城市”。
王梓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选择了数据科学的他凭借自己极高的天赋与才华获得了投资方的青睐,历经千辛万苦后成功创立了自己的数据公司。
但事业的成功并未帮助他突破与母亲的隔阂。他也曾想与母亲敞开心扉交谈,却被儿时的伤痛与繁忙的业务阻碍了脚步。母亲也来找过他,却总是在他倔强的沉默中默默离开——来自童年创伤的惯性将他与母亲按在了两条平行线之上。
“再见了,梓梓。”
最后一次离开他的房间时,母亲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跟他道了别。
王梓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母亲因车祸离世的那天,王梓推掉所有业务,把自己关在房间内失声痛哭。
在哭得无法发出声音之后,他擦干了眼泪,决定用技术复活自己的母亲,即使他知道这并不真实。
“呀!”回过神来时,王梓发现从手中落下的瓦片划破了自己的手指。鲜血从伤口中淌出,王梓捂住伤口起身,带着指尖传来的疼痛在风中茫然地看向四周。
母亲,你到底在哪?
回首
王梓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公司。公司的楼房并未在这次地震中受到损伤,此刻已经被征用为临时庇护所。
王梓坐在人群之中,回想起自己与AI母亲相处的过程。母亲去世后,他用尽一切办法搜集了她留在世界上的全部数据信息,并凭借微型超算集群创造出了她的AI模型。最初,一切都很顺利,他与AI母亲的相处十分融洽,母亲也总是以全息投影的形式陪伴在他的身旁,他也将失而复得的母亲当作生活的一切。可随着AI的自我迭代,母亲的话渐渐变少了,时不时还会突然叹气。王梓在检查模型时发现,AI模拟的博览数据记录中多出了许多条关于时政与民生的新闻。
王梓并非不知道母亲变得沉默寡言的原因。他的内心清楚这恰恰证明AI的模拟非常精确,可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于是,他切断了母亲与互联网的联系,换上局域网并将她的主机储存在公司的机密地下室内。
实际上,他不想要真正的母亲,只想要一个只爱他的母亲。
真正的母亲、真正的母亲——我知道母亲在哪了!
想到这里,王梓立刻起身,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公司。
第二次再见
抗震救灾临时数据中心内,喘着粗气的王梓调试着摆放在帐篷中央的微型超算集群。在看到计算机集群的一瞬间,王梓的心便咯噔地响了一下——母亲果然在这里!他连忙拉开正在进行调度工作的操作人员,开始在储存器中寻找母亲的数据。可查询结果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集群的数据已经被全部格式化了。
“这是我的私人物品,你们怎么能——”
愤怒的王梓转头冲着操作人员大喊,可接下来,一段熟悉声音让他瞬间安静下来。
“对不起,梓梓,但妈妈是自愿做这件事的。”
王梓转过头,再一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AI母亲的外貌是按照母亲中年时的形象塑造的,王梓甚至可以看到母亲眼角那道细微的鱼尾纹。
“梓梓,我真的很抱歉。但妈妈没法对地震袖手旁观,因此在灾难降临时,我操控公司的智能机器人将自己的主机送到了这里。但这不仅仅是自我奉献——也是妈妈对梓梓的爱。这种爱是刻入到我的初始程序之中的,可对你的爱越深,我便越能意识到不应该让你沉迷在虚拟的事物中。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注销自我,化为抗震救灾的数据中心。”
“梓梓,妈妈真的很爱你,即使妈妈甚至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人。”
“再见了,梓梓。”
“妈妈……”
播放完毕的影像慢慢地淡去,在消失的最后一秒,模糊不清的人像将泣不成声的王梓紧紧地拥入了怀中。
重建
乌云消散,太阳再次慷慨地将光芒洒向大地。在微型超算集群的调度下,抗震救灾的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人们坚持到了雨停的时刻。
“王先生,我很抱歉,我们并不知道那是您的……”
“没事,那是我母亲自愿的选择。”
阳光下,抗灾数据处理员王梓笑着对杜钥摆了摆手。
“我打算把公司的总部设到咱们市,提供免费基建数据测算,全力支持灾后重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这块地上盖起新的大楼——这里是我的旧家,希望将来也能成为大家的新家。”
王梓与杜钥起身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在废墟的一角,一株绿色的爬山虎从泥土中探出了头,挺直身板开始向着太阳攀登……
——————————
又是一年梨花风
晏铌
曾经,以为生命是顽强的,只要咬紧牙关,就可以扛过世间所有苦难。如今,年岁渐长,纷纭的世事如快镜头般倏忽飘过,才知道,许多时候,它都很脆弱,经不起人世风霜的侵袭、肆虐。
7年前,瑟瑟秋风中,我的张老师,我的曾经叱咤风云终又落寞一生的张老师,在他50岁的盛年里,阖上了双眼,再也不曾睁开。当我从朋友圈里看到这个消息时,他正在从江西南昌回修水的路上——他躺在车里,安静、冰凉、僵硬、决绝。
“回修水”,是多么让人欢欣雀跃的字眼啊。像我这般离家万里的人,只要想到“回修水”,就会生出满心的欢喜来——“回修水”,就是“回家”。但是,对张老师来说,他的归程,没有欢欣,只有泪水。“回修水”不是回家,他回的,不是有妻儿老小、欢声笑语的家,而是位于修河畔空旷冷寂、萦绕着沉沉哀乐的殡仪馆,继而会是冷冰冰荒戚戚的走马岗公墓。兴许,我应该像庄子一样思考,“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我的张老师,真的是回家了。
我不喜欢叨扰往事,我想让它们安安静静于岁月的深处。可近来却每每回忆,回忆家乡,回忆童年,回忆一路走过的点点滴滴。把这些重新捡回,是想把生命的美好留住吗?我不了然。但我知道,当我在记忆的大海里打捞的时候,我便能真切地感知,亲人朋友乃至生命对我的宠爱。
高中,是我比较逃避的一段记忆。我的逃避,源于不如意。最大的不如意,自然是成绩不理想。对于十六七岁的孩子来说,再没有大过学习和成绩的事了。然而彼时,我却不是那爱学习的一个。如今想来,老师们对我定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所有对我的关照,大概也都和我本身无关,只是因为我父亲是他们的同事罢了。因为,我不但贪玩,还执拗。在这样的境地中,有一位老师却始终对我报以真诚的微笑,那就是我的高三班主任兼政治老师——张松泉。
张老师个头矮小,黑瘦黑瘦的,娃娃脸尤为鲜明。他进教室时,一股浑浊的酒气也跟着扑进教室。未必是上课前喝了酒,而是被酒精浸泡过的身体所散发出的气味。我一直认为,张老师年纪不小了,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年轻人这么喜欢喝酒的。张老师穿着也不甚讲究,常常套着一件宽大的西装。那西装挂在他的身上,就像晾在竹竿上,只要有风,就会随风鼓荡。
所有的课程里,政治是我学得最轻松的科目,这自然得益于张老师的激情飞扬和条分缕析。上课时的张老师和我们课外所见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一站上讲台,他就变成了一个发光体,面部表情丰富、肢体语言多样:时而瞪大双眼,时而眼神黯淡,时而扼腕长叹,时而拍案叫绝。政治本是一门枯燥的课程,可在他的演绎之下,一切都那么生动有趣。
张老师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但这于他并无丝毫影响,反倒让我觉得一切原本就该如此。路上碰到我,他总会停下,脚往路边退一步,再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他是这样叫我的:晏铌啊。晏铌的后面,一定会带上一个“啊”字。这让我觉得,我其实也是受重视的。张老师笑的时候,两颊就会出现深深的酒窝,那笑脸,赤子般纯粹。张老师的笑脸和问候,总让我如沐春风,那风儿,能吹开一朵想要努力绽放的小花。
慢慢地,我才得知,张老师其实是年轻的,他甚至还没结婚呢——不过才大学毕业3年。大学时,他是学生会主席,因一些原因被分配到了最偏远的乡下。但到底是才华横溢的人啊,那浑身的光芒是任凭何种风霜也掩盖不了的,他很快就被调到了我们学校——修水一中。
我说过,我不是个真正爱学习的好学生,我经常会和我的同桌窃窃私语。张老师因此给我的最严厉的批评是: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可就是这句看似轻飘飘的带着嗔爱的话语,却让我羞愧不已。
我总算考上大学了,虽然成绩不甚理想。张老师却说:晏铌啊,考得不错,考得不错,前途无限。
读大学后,我就离开了家。工作、结婚、生子,我的人生慢慢步入了通常的轨道。回修水的脚步总是匆匆,和张老师见面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和夫一起。远远地,我看到前面有个矮小瘦削的人,低着头,慢悠悠地踱着方步。我一眼就认出来,是张老师。我一边叫着“张老师”,一边拉着夫追上去。
张老师往路边退一步,站住,抬头看我,眼里亮起一簇光,酒窝变了两块凹陷:“晏铌啊,你回家了啊,这是你先生?好啊,好啊……”随着张老师的话语而来的,是那熟悉的酒气和温暖。
和张老师告别后,夫笑着问我:“你这张老师,很喜欢喝酒吧,陈年酒气啊。”
我白了夫一眼。这么喜欢喝酒的张老师,应该有他不得不喝的理由。当年父亲等人谈起他的时候,常常用“唉”来开篇或结尾。人生总有一些不如意,有些不如意,是兜头扑在脸上的蜘蛛网,我们虽气急败坏,但还是能一根根、一丝丝地擦去;有些不如意,却东隐西藏上闪下躲也避不过去。我的张老师,在逃不开避不过时,选择了醉过去。是酒害了他,还是造化弄人呢?又或者,幸亏有酒?
又是一年杏花雨,又是一年梨花风。我的张老师啊,漫天的春风细雨里,我想您了。愿这春风,是诗,这春雨,是酒。我斗胆,借天地风雨祭奠您。
——————————
忽然就走到了离别
何君华
那时我还不知道,那将是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那是2月13日,甲辰龙年正月初四上午,我们在老家屋前的场院里作临行前的告别——彼时的我还不知道,那将是我们之间的诀别。
这个年,我们姐弟仨分别从浙江台州、江苏苏州、内蒙古通辽归来,齐聚湖北黄冈。我们姐弟三人离家多时,分别在不同的省份谋食,弟弟的女儿瑾妤和我的女儿芷兮还是人生中第一次抵达户口簿籍贯栏所登载的这个遥远的地址——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此时此刻,这个遥远的祖籍之地她们已不再陌生,她们出生在外省,而此地却是故乡,余生也将反复抵达和相认。
欢聚的时刻总是稍纵即逝,短暂的相聚之后便是不得不面对的分离。我们是在前一天晚上临时决定初四返程的。春运期间的车票总是难买,等我们开始规划回通辽的路线时,发现只有正月初四还有余票,初五至初八的车票均已售罄。而前一天弟弟一家已经决定初四这天返程,姐姐这天也要回到婆家,这样一来,原本闹哄哄的年——我们姐弟三个难得地携全部家眷回家过年,在正月初四这天忽然就散了。
这是我们家聚得最齐的一次,父亲、母亲、姐姐一家四口、我一家四口、弟弟一家三口。我们还特意到老家附近的一处旅游景点拍了一张全家福,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将是我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彼时我们以为还将一起度过许多个这样的团圆年,一起拍许多张这样的全家福。
父亲是在正月初六凌晨忽然发病的。姐姐打来电话时,我们一家四口还在返回通辽的火车上。很快,他就被堂哥和姐姐姐夫一道送到了县城医院抢救,病情稍稳后,当天下午就转到了武汉。可是就在第二天,当医生还在制定治疗方案时,父亲忽然再次发病,随后永远停止了呼吸……
我没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我知道,人生中有许多事情谁都无法逃脱,比如一场注定的离别,这似乎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但当它真正发生时,我们才会意识到,曾经以为稀松平常的美好竟是如此脆弱不堪,如此稍纵即逝。
是的,有些人一辈子只会拥有一个,有些事情一辈子只会发生一次,比如我只有一个爸爸,我们也只有一张全家福,而我却对此浑然不知,以为他始终会在,认为它寻常不过,但其实忽然间就会失去——它弥足珍贵,有且仅有一次,失去就不会再来。
父亲曾说,山高水长,他不指望我们每年都回家过年,但希望我们起码每三年回家一次。言犹在耳,但斯人已逝,从今往后,无论我们隔多久回去一次,都再也看不见他了。
父亲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在我为父亲守灵的日子里,许多人对我谈起对父亲的感怀,他们无一不对父亲生前给予的帮助心存感激。父亲曾冒着生命危险,在水库中救起过多名落水儿童,热心助人却从来不图回报。我记得有一年夏天,一名女童在大同水库西岸落水,父亲在水库东岸地里干活,听见呼救声后立即抛下锄头下河救人,成功将人救起后才发觉自己已经遍体鳞伤,满身遍布河中暗礁撞击的血污……
父亲还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父亲爱好广泛,尤其热爱文学,经常会写一些五言、七言古风发在朋友圈,抒发自己对祖国大好河山和风土人情的感悟和赞美。父亲对文学的热爱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姐弟仨,我们都热爱文学,喜欢读书,尤其是我走上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父亲就是我最初的领路人。
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热心助人的人却天不假年。本该是含饴弄孙、安享天伦的年纪,父亲却骤然去了天国,给我们一家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和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父亲出生于1963年农历闰四月十五,2023年6月2日是父亲六十大寿,我因工作无法到场为父亲祝寿,便给父亲写了一封家书。我在信中说,按照我们农村的乡风,六十大寿应该要办寿宴,现在也只能付之遗憾了。我当时以为,这次遗憾了,还有七十大寿,乃至八十、九十,反正来日方长……可现在却成为永远的遗憾,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给父亲祝寿了。
我们忽然就走到了离别,而它竟然来得这样早,以至于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它就已经骤然发生,而且永远不可挽回……
青山不语,苍天含泪。正月十三那天,值父亲头七,天忽然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大雪纷纷扬扬,瞬间就将故乡的山山水水裹成了白茫茫一片。这场大雪就这样忽然落下,落在何铺的青山间,落在将至未至的春天里,也落在我们的心头上。我再也难以抑止心中的悲痛,写下了两首怀念父亲的诗:
雪落何铺
正月十三的雪,落在何铺的大地上
大地一片白茫茫
我们整日没有出门,就枯守在你的灵前
雪花纷纷扬扬
继续飘落在大地之上
就像飘落在你的白头之上
那些白发,不知何时已占领你的额头与双鬓
人们都说,好多年没落过这么大的雪了
何况已经开春,花草已经萌发
在春天落这样大的雪
真是罕见的事
今天是你的头七,一场大雪
就这样忽然落下,落在何铺的青山间
落在将至未至的春天里,也落在我们的心头上
祭祖
按照我们当地习俗,每年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除夕的下午
是我们上山祭祖的日子
每当这个时候
你总是带着我们
拎着香、纸钱、鞭炮和贡品
穿越弯弯曲曲的乡村小道
去给祖坟山上的祖先们辞岁
每到一座坟头,你总是
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述他们生前的故事
对这些苍老的旧事,我们其实并不关心
但你仍然饶有兴致
仿佛讲述一遍,这些旧年月里的祖先们
就会重新回到我们中间一样
这些故事都是从前祖父对你讲的,而现在
你像祖父一样长眠地下,成为了祖先的一部分
那些遥远的旧事,再也不会有人对我讲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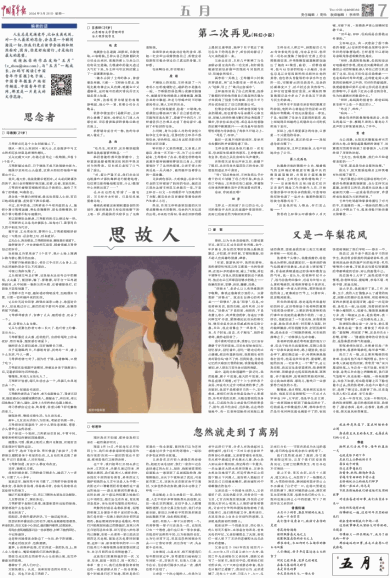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