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秀群在还是个少女时就嫁人了。
她从一座大山来到另一座大山,长途跋涉中与丈夫的相互扶持算是新婚的赠礼。
丈夫比她大8岁,在她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并留下3个孩子。
刀秀群嫁过来后,日子继续不咸不淡地驶向前方。
她偶尔会站在山头遥望,试图从相似的绿海中窥探出什么。
某天,遇大雨,泥屋受潮后更阴冷。丈夫是沉默寡言的男子,他只会用臂膀环抱住她,忍着,忍着,直到天明。
刀秀群听着噼里啪啦的雨点开始明白,她有了不得了的情感,叫做思念。
思念是一种暴力的情感,极其容易闯入心房,而后开始胡乱碰撞,直到留下满目狼藉。
不过,庆幸的是,刀秀群是个平和内敛的女人。她鲜少展示情绪波澜,笑也是微微的,烦也是微微的,好似万事万物都不配令她侧目。
所以即便思念肆虐,刀秀群仍然可以接过每一招。
刀秀群的丈夫是名赤脚医生,每每出门,需要用许久的不相见为代价。
离开前,丈夫常会问,要带什么。刀秀群细细碎碎说过一大堆后,总会附上句,回来就好。
丈夫点头,然后便走,刀秀群则转身,继续留在老屋下。
她带着孩子,守在老破的瓦房里,捱着情感从背脊划过的岁月。
后来她又为家里添了5个孩子,狭小土地上围满以她为圆心散开的血脉。
刀秀群开始倾斜重心,将自己专注在儿女身上,以为这样她的思念可以不再漂泊。
可惜刀秀群失策了。
丈夫被地主叫去打牌,这是场永远没有公平的赌局。丈夫赢了,能回家;输了,要跪着,双手合十后再被绑起来,从中间插一根削尖的木棍,忍着痛继续打,打到地主觉得他赢了。
刀秀群不言不怒,她知道动情绪没用,但她擅长习惯,习惯一切向她冲来的东西。
丈夫有天没有回家,病倒在某条山路上。他医治许多人,却没救过自己,糜烂的双手要对外宣称,是摘草药留下的痛。
刀秀群带着孩子,安葬了丈夫,她的思念,死去了一个。
家,总要有人去支撑。
丈夫与前妻生的老大老二长大了,他们背上行囊,走出大山。
刀秀群像送丈夫般,送别他们,话语结尾附上回来就好,然后转身,继续留在老屋下。
她的思念又漂泊起来,还好她擅长习惯。
日子是瞎眼的犬,不顾地向前。突然有一天,撞上什么东西,吓人一跳。
刀秀群的老七死了。因为肚子饿,去逮蜘蛛,火烧了吃下。
刀秀群还是那副平淡模样,带着其余孩子埋葬老七后,又重新回到生活的轨道。
慢慢地,其他儿女也长大了。
刀秀群计划着,隔几年送出去一个,再隔几年再送出去一个。
可惜,计划最没有诚信。
刀秀群的老四去了城市,老五也跟着去了,等老五回来,她说她动心隔壁城镇的男人,她嫁走了。再后来,老五回来拽走了老六。隔年,没考上大学的老幺也跟上脚步。
待刀秀群反应过来,转身看,家里只剩下好吃懒做的老三。
她很淡然,继续过着生活,与从前无差。
新年,儿女会从四面八方回来。老屋会热闹一阵。
刀秀群依旧那副样子,对什么事仅是抬眼,看看,点头便带过去的态度。
日子形成一个轮回,刀秀群站在其间,不管不问,接受种种相似的瞬间同她擦肩。
她擅长习惯,围满土地的人散开又聚拢,对她而言仅是固定行踪的运动。
新日子,政府下发补助,帮忙修建了新房子,刀秀群得以摆脱委身于老屋的生活,儿女也在周边盖了新家,不过只是盖着,人还在他城。
刀秀群知道,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还好,她擅长习惯。
我有时候会想,刀秀群能习惯多久。她活了八十多年,习惯了八十多年。
直到去年,她突然不再习惯了。刀秀群开始变得情绪多变,容易哭容易闹,容易离开家,容易无助地停在某处陌生的地方。
她记不起周遭的一切,所以习惯的本领也自动解除。
儿女都回来了,围在身边。
刀秀群想不起他们是谁,她重新望向远处的绿海,即便那里什么也没有了。
我也回来了。
妈妈说,多跟外婆讲讲话,万一她记起你来。
我尝试和外婆说自己的名字,她先是疑惑地看着我,再是抗拒,而后又是小心尝试,最后颤抖着唇,试图发音。
而我在发现她眼里闪过一丝哀愁时,打断了她的回忆。
不记得最好。
这是神对她受思念胁迫了一生后,给予的恩赐。
外婆走时很安详,也算圆满。
夏季,山雨细碎连绵,打在排成一条的队伍上。男人女人低着头,嘴里唱着我们民族的歌谣。
那些空灵又陌生的音符从山头连到山尾,送完外婆最后的旅程。
墓碑安下,同人们对立。
大家低着头,从此,该承担思念的另有其人。
反正,再也不会是刀秀群了。
冯嘉美(2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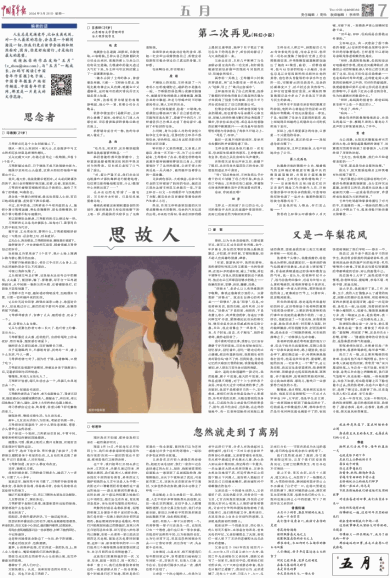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