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嫩艾叶淘洗干净,切碎,放入料理机。然后她取来清水,缓缓注入,艾叶碎散在清水里,新鲜郁绿。窗外,风伸着柔软的小舌把大地舔得温和柔美,知时节的小雨把春天洗得清澄明澈。
清明,一个多么柔美新鲜的词。每年这一天,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做一些清明粿。
“滋——”艾叶化为碧绿的浆液旋转飞舞。她望着那绿团,思绪回到了那年。
那年清明,父亲回乡祭祖,顺便把6岁的她交给了阿婆。她望着父亲的影子朝远处流去,笔直而流畅,只好把委屈生生吞下去。阿婆刮刮她的鼻尖,揽住她,那份揣在心窝的小心给她吃下一颗定心丸。
“年年艾叶绿,岁岁粿飘香。阿婆给妞妞做清明粿。”小小的石磨在阿婆手里转啊转,艾叶浆汁从磨槽里缓缓淌下。她抱着瓷盆小心接着,眼里充满期待。
拿出糯米粉和粘米粉,然后把料理机里的艾叶汁一点一点分批倒进米粉里。她手执竹筷,细细搅拌,然后小心揉搓,让米粉与水慢慢混合,最终成为一个光滑的面团。雨声窸窣,像远处沙滩上的潮水似的,一会儿漫过来,一会儿退下去,轻轻拍打着她的耳膜。悠悠地,她的眼前浮现着与阿婆一起揉面的样子。
小小的她嫌阿婆揉得太慢,便伸长了手去帮忙。她哪是帮忙,分明是捣乱。阿婆按着她的小手教她揉面,艾叶浆汁把米粉染得碧绿,像把春意染了进去。她哪耐得住性子,揉不了一会儿,手就开了小差。于是,阿婆差她剥笋衣。她把笋衣剥的哧溜溜响,引得阿婆眉眼含笑,“我们妞妞真能干,剥出了又白又嫩的春姑娘!”她的小脸顿时起了一层粉雾,心彻底被拽向了阿婆。
她把馅料炒熟,再将蒸熟的面团取出放凉。然后搓剂子、擀皮子、包清明粿。左手托住面皮,右手拿调羹放馅料,然后两手合作,飞快地捏出花边。这是千百次的熟生出的巧。阿婆如果看到,肯定会说这句话。把清明粿摆进蒸锅里,然后打开炉灶。火舌跳跃着舔舐锅底,她坐下来,靠着椅背,细听蒸锅里渐渐风起云涌,思绪兀自向记忆深处回溯。
记得那天,雨下得很有耐心,丝丝缕缕的,把整个大地都笼在朦胧的薄烟里。蒸汽推搡着锅盖,发出一阵噗嗤噗嗤的声响——清明粿熟了!她刚生出几分亲近的目光还没长足勇气,怯怯的,不敢把心里的馋说出来。阿婆打开锅盖,夹出一只清明粿,从左手颠到右手,再从右手颠到左手,颠得它热气渐消,然后放在她的小手里。清明粿像上了层绿釉,亮得饱满,水水的、滑滑的。她轻咬一口,糯糯的、暖暖的。那一刻的幸福是那么珍贵,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幸福得几乎眩晕。吃完一只,又吃一只,她的委屈彻底结了痂。风清雨细,阿婆的笑意绕着她,那一刻,6岁的她猛然领悟到气味和笑意,甚至沉默,都是一扇门,能把人带进另一个人的心里去。
一刻钟后,清明粿熟了。她搛出一只,也像阿婆那样,从左手颠到右手,再从右手颠到左手,感受热气从指尖溜走。她细细地吃,熟悉的味道在唇齿间游走,那扇被时空锁上的门再次打开,她抱住自己的身子,像当年阿婆搂住自己,然后迈过门扉,回到了有阿婆在的那个世界。在回忆的剧场里,心被思念和哀伤撕成两半,又被清明粿的香味抚揉成一团,渐渐熨帖平静下来。
石磨转啊转,她渐渐长大了。初潮袭击时的慌乱,第一次收到情书时的羞赧,考试失利时的悲伤……阿婆陪她闯过每一个关口。
忆及来路,她不禁莞尔一笑,拿起一个清明粿,细细品味。可吃着吃着,她的泪落了。
“阿婆病危,速归。”她连夜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带着满身风尘,见阿婆最后一面。
阿婆躺在老屋里,用衰颓的目光把她抚摸了一遍又一遍。她用目光捉住阿婆的目光,把“不舍”说了一遍又一遍。似乎冥冥之中有安排,那天也是清明节,雨下得黏黏糊糊,把生离死别渲染得悲悲切切,阿婆最终还是闭上了眼。她望着摆在案台上的清明粿,一只压着一只,翡翠般油亮。她想,阿婆不会孤单,有清明粿这扇门,阿婆随时可以找到归途。
被雨水淋湿的阳光洒在碗沿上,泛起浅绿色的光,清明粿还有最后一只。它的香气被清凉的空气萃取出来,袅袅艾香绕在她的心门。她知道,那是通往阿婆的世界的门。她坐下来,深深闻嗅,仿佛听到“吱呀”一声,然后隐约看到墙角边的木桌上,正兀自放着一盘清明粿。
陈雪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二中附校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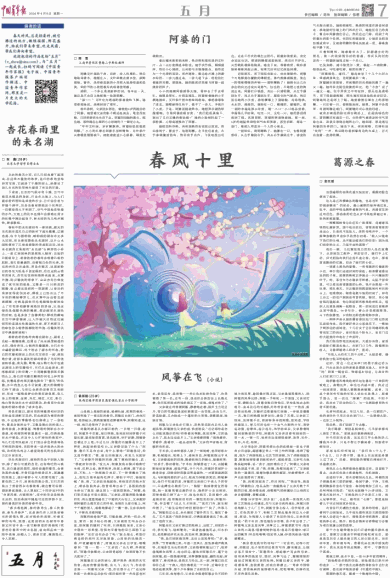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