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母亲的爱,是一种默默的奉献,是一种无尽的关怀;母亲的爱,如潺潺溪流,润泽着我们的心田。在这个母亲节,这些青年用笔传达情感,用这份特别的礼物来表达对母亲的深深爱意。
——————————
如果母爱有赛道(随笔)
张喆
我的嘴边有一个小小的痣,都说这是爱吃的象征,我是相信的,因为就连小时候去诊所,我也会因为讨厌嘴巴里停留的苦味,在吃药和打针中选择打针。
吃药难,喂药更难。妈妈对于这件事怨念颇深,在她的记忆里深刻地记录着两次滑铁卢。其中的一次我没有记忆,据说是小时候看到她冲感冒药后,为了不吃药就偷偷跑出了小院儿。妈妈吓得追到街上时恰巧被前院儿的婶婶看到,结果不仅被冤枉“发火吓到了孩子”,还被迫接受了一场“对孩子永远不能发火”的育儿教育课;另一次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得了胃炎,中药太苦,我喝了就会吐,妈妈把吃糖吃橘子等方法一一试过都无效后,忍不住大声说了一句:“药还有好喝的?快喝!”结果又被爷爷奶奶说成是“发火吓到了孩子”,再一次接受了一场相同的“对孩子永远不能发火”的育儿教育课。
她磕磕绊绊地学习着成为妈妈,在她的眼里,我的生活是无数的起跑线,学着吃饭、走路、上学……不管出发早晚,不管速度快慢,她只是陪我摸索着向前走。若是母爱也有赛道,也不知现在的我,陪着她走到了哪儿?
小时候,我和妈妈像是天生“对手”。如果我学过画画,那么我会把她画成瞪着铜铃大眼的钟馗,把自己画成一只可怜的小鬼;如果我是作曲家,那么我送她的也绝不是恬静的钢琴曲,而一定是一首激烈的摇滚……现在的我和她,更像是一对相爱相杀的知己,高手过招,各有输赢。现在我已经有些“后浪居上”了,她出门时,我成了那个絮絮叨叨、反复进行反诈骗宣传的人;她要去医院,我成了网上挂号又带着她去排队、分诊、取药的人。
我听过也看过太多关于母爱的影音和文字,那些隐藏在平淡中的重感与温情,爆发在转折中的力量与柔韧,那些母亲的形象是相似的,像是天生的奉献者。但书本合上、屏幕变黑,那些虚幻的母亲形象就会淡去,她们都不是我的妈妈,我拥有的只有眼前的她而已。
她是个“小孩儿”一样的少女,现在也依然喜欢看甜甜的爱情小说和偶像剧,喜欢宅在家里围着厚厚的被子刷手机。我也在学着认识她,原来她会站在那些对于我来说便捷快速的机器前面束手束脚,会用那些蹩脚的借口拒绝去看病吃药,也会轻信别人买回“三无”保健品。
记得有一次领了奖学金后,我决定给妈妈买条裙子,大概她嫌价格太贵,于是站在身侧悄悄拉了拉我的手肘,我悄悄抓紧她的手轻拍,正如我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无论何时想回家,只要悄悄抱住妈妈的小腿,就会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我。
小时候,爱是她的大手牵着小手;长大了,爱是我坚定地与她五指相扣。转眼间,这条爱的赛程已经走了很远。现在回家聚餐时我是有几个专属禁忌词的,尤其是对着侄子侄女时,如果提到“惯着他”“不懂事”“我当时”等诸如此类的几个词,那就像是打开了暴晒后又剧烈摇晃的一罐可乐,妈妈就会从一句“你还说别人?”的强烈疑问句开始,直到说出我20件糗事后的一句“我都不稀罕说你了!”的感叹才能结束。她的“历史事件记录簿”像是一个可回收的环保炸药桶,只要对象是我,那能量一定随时满格。多年经验积累下来,我甚至有些怀疑书本上那些关于记忆遗忘曲线和能量守恒定律的说明。
我的表达能力远远比不上爱读书爱写字的她,所以我写过太多太多的人,却很少写她。也许是因为我依旧稚嫩,还没学会将自己抽离,以一个旁边者的身份去观察记录;也许是嫌弃每一个文字,疑问它们为何不能表达出我对于她的全部感受。她是母爱森林里万千树叶中唯一的一片,甘愿在我的人生之书中风干。我吸收她青春的水分,给她增加一些褶皱;她将自己拆解为细密的纤维,为我织补出一页又一页新的篇章。
——————————
母亲,母亲(随笔)
沙玛妈尔(彝族)
《请回答1998》中,有一段令人泪目的台词:“听说上帝不能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到了妈妈的年龄,妈妈依然是妈妈的守护神,妈妈这个词,只是叫一叫,也触动心弦。”但是我对我的母亲,惯常不爱称之为妈妈。我总是说母亲,母亲。
与“妈妈”相比,“母亲”这个词就显得冷淡、有距离。虽然“妈妈”自带温情而显得温馨,但是我只愿以“母亲”在他人面前介绍她,我觉得更显分量,也更显厚重。
我的母亲和世界上其他千千万万的母亲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她较其他人,更加平凡,更加普通。
她没我高,生过3个孩子,略微有一点胖,头发本来只是有点黄,在她多次染黑后,变本加厉,成了金黄黑三色驳杂的发色,于是她也不再纠结于发色,任其发展。
过去生活艰难的时候,我很少能和她在一起。她操持着一家子大大小小所有的事务,早出晚归,地里的农活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春季采茶、摘蕨菜贴补家用,给我们姐弟挣学费;夏天有时候晚上都要在田里守着水,不能让别家把水截了去;秋天就更忙了,要收苞米,收稻谷,收完自家的也要去别家帮忙;冬天似乎总算能歇息一会儿了,也要去山上砍些柴回来。一年四季,她永远在忙碌,而我们没上学之前,就在房前屋后自顾自地玩耍,爬树摔了,不会有人扶起,甚至一直到伤好了,母亲也不见得能发现。
曾经,看见别人的母亲,我是羡慕的。后来,我又懂了,她以瘦弱之躯,给我和弟弟撑起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我只是没有零食,没有花花绿绿的衣服,但我吃饱穿暖,并不曾因为贫穷而挨饿受冻。
或许贫穷仍然在我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比如我备受友人打趣的“抠”。但节俭本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呀。而她,在我之前,替我挡尽了来自这个世界的诘难,她挡不住的,我又如何能怪罪她。生而为人,当有一颗感恩的心,去感知这平凡世界里所有的小幸运。
多少同龄人在小学、初中便辍了学,而我,已经上了大学。在求学之路上,我最开始是懵懂,即使家里不让我上学,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那时候的我,并不懂得教育和学习是什么东西。后来,我懂得了,她也并不曾因为任何原因而对我说过:你放弃吧。
我感念她。在我不懂事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儿,那样叛逆的日子里,不止一次地伤害过她。她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女子,她同农村里其他所有的女人一样,一辈子都是丈夫、孩子、家,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可是她又与那些女人不同,她爱八卦,但是不爱说人长短。
她,是一个母亲,她身体力行,教会我许多道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念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并不太懂得这句话背后的沉重。后来我离她越来越远,看见她一个人的孤独,看见她虽然孤独但是又与人“话不投机半句多”。我突然心疼她,她是一个母亲,也是一个女人,但她没有什么爱好,只能在子女成人后日渐清闲的日子里,越来越孤独。她年少的时候以长女的身份、长姐的身份存在,弟弟妹妹都上了学,她便跟着父母操持家务。后来做了妻子、母亲,又围着丈夫和子女转,她这过去的前半生,其实鲜少作为自己而存在。
岁月如水淌过,在她的眼角眉梢都留下了痕迹,白头发也悄悄冒了出来。她不过是40多岁的女子啊……我时常害怕,害怕自己成长太慢,而她等不及我长大。幸好,时光待她以柔情,不再操劳的日子里,她往年因为过劳而导致的各种健康问题都渐渐好转。而我,只是担心,我们都不在她身边的日子里,她是否会孤独。
妈妈是心底的柔情,母亲是护住儿女的强硬。她是水做的女人,有时也是如冰凌一样坚硬的母亲。
人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每每念及她,那个如同寻常母亲一般强势的、固执的、能干的女人,我都会在心底默呼:母亲,母亲。一声又一声,唤她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我,唤她在贫苦中养育我,唤她免我饥寒又给我建造一个精神的世界。
母亲,母亲,一声又一声,不只是来路,也是归途。
——————————
老照片里的母亲(随笔)
姜燕
母亲当了18年的小学教师,每年学生毕业,师生都会一起拍毕业照,相册里留下了不少她执教时的老照片。
老照片都是黑白的,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已经斑斑驳驳,看不真切了。一张1974年的毕业照里,母亲梳着两条麻花辫,穿一件斜襟的格子小衫,坐在学生们中间微微笑着,清秀恬静。彼时的母亲还未嫁人,比她的学生们也就大个十来岁,还是个20岁刚出头的姑娘。那时的母亲瓜子脸,丹凤眼,不胖不瘦恰到好处,有着那个年代女孩特有的羞涩,看上去像女文青,清秀而文静。
一张1982年的毕业照里,母亲剪着齐耳短发。那时我大哥、二哥正调皮,可能是又要带孩子,又要教书比较辛苦的缘故,母亲看上去有些清瘦。照片中的她,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灰色的春秋衫,因为身材瘦削,外套略显宽松,但仍是嘴角含笑,比起做姑娘时多了一些少妇的韵味,美得不惊艳却让人过目难忘。
1989年的毕业照里,母亲圆润了些,留着学生头,还是白衬衫外罩着一件外套。外套上大格子的图案,加上母亲灿烂的笑容和学生们纯真的笑脸,使母亲看上去明媚而大方。母亲拍照很喜欢笑,几乎每张照片都是笑着的,这个习惯影响到我,每次拍照对着镜头不由自主地就笑了起来。
母亲的老照片不是师生一起合影的毕业照,就是全校教师合影照,在那个只有黑白照片的年代里,母亲没有拍上一张单人照,一直是她的一个小遗憾。
时间的轮子不停地转着,转走了母亲的青春岁月,也转出了一个女子如花般盛放又逐渐老去的生命轨迹。如今,母亲教过的学生都已经人到中年,母亲也到了古稀之年,家里的旧物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都慢慢消失,唯有这些老照片还躺在母亲的相册里,粲然生辉,闪耀着温润动人的光泽。
母亲闲暇的时候,常于无人处,戴上老花眼镜细细端详着那些老照片,用曾经握过粉笔、执过教鞭现今皱纹纵横的手慢慢摩挲过每一张照片后,又悄然叹息一声放下。我知道,那是母亲又想起了她回不去的最好年华。
这些老照片里有母亲的过往,也有母亲的念想,它们见证了母亲的青春,在岁月长河里留下了母亲最美的倩影。
——————————
妈妈的书信(童话)
姜士冬
温煦的阳光照拂着森林和大地,透过林中细碎的树叶,变成一束束金黄色的光。
“我有一把神奇的钥匙,它可以打开世界上的任何一把锁!”猪哩哩站在一棵树下说。
鼠小弟提出异议:“不是说,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吗?”
猪哩哩摇摇头:“那是普通的钥匙,而我的这把可是神奇钥匙。”
“难不成是仙女姐姐喜欢你,单独送给你的?”
“不是,这是我爱搞发明的猪爷爷创造出来的。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猪爷爷便把它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我了。”
“原来是猪爷爷呀,他可是一位大科学家,那看来你的这把钥匙确实有可能打开所有的锁。”小猴子在一旁说。
“哎呀哎呀,猪哩哩,快来帮我打开这把锁吧。”山羊爷爷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手里捧着一个铁箱子,上面还有一枚生了锈的大锁头。
“这把锁的钥匙呢?”猪哩哩好奇地问道。
“早在十年前就丢掉了,我翻来覆去地找,把房子翻了个遍也没找到。”山羊爷爷继续说,“这箱子里可有很重要的东西,我已经有十年没看过它了。”
热心肠的猪哩哩急忙从裤兜里拿出那把神奇钥匙,很轻松地便插进了大锁头的锁眼。猪哩哩轻轻一转,锁头就被打开了。
“哇,果然是一把神奇钥匙!”鼠小弟不禁感叹道。
猪哩哩打开箱盖,只看到一张泛黄的纸,其他什么都没有。
“山羊爷爷,我还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原来就是一张纸呀。”
山羊爷爷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纸拿出来,轻轻地摸了摸,顿时红了眼眶:“你们还太小,很多事还不懂。对我而言,这张纸可比什么财宝都珍贵,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时,我的妈妈写给我的信。”
小猴子说:“妈妈的信有什么珍贵的,妈妈每天都和我说好多话,我都快被烦死了。以后,我一定要离开家,离妈妈远远的,再也不想听到妈妈的唠叨声了。”
鼠小弟也附和道:“对呀对呀,妈妈是天底下最唠叨的,我可一点都不喜欢妈妈的话。”
山羊爷爷咳嗽了几声:“等你们长大后,就会想念妈妈的话了。钥匙没丢的时候,这封信我每隔几天就要拿出来读一读,信中满是妈妈对我的想念。妈妈说,儿子,独自在外,要照顾好自己,不要饿到冻到,要按时吃饭,天冷加衣……”
“我听了半天,妈妈也没有说想念你呀?”鼠小弟说。
小猴子也说:“一个想念的字眼我可都没听到。”
猪哩哩擦了擦眼泪:“说了说了,我听到了,妈妈在信中写满了对儿子的想念。”
山羊爷爷摸了摸猪哩哩的头,说:“谢谢你,以后我又能常常读到妈妈的信了。”
临近中午了,鼠小弟、小猴子和猪哩哩的妈妈都大声喊道:“孩子,快回家吃饭啦!”
这一次,三只小动物也不知道怎么的,突然觉得妈妈的呼喊声是那么亲切,那么温暖,如同这林中的一束光。三只小动物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只留下山羊爷爷,捧着书信,思念着自己的妈妈。
——————————
母亲,是我内心深处最温暖而铿锵的力量(随笔)
许志昊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望着窗外绵绵的细雨,我冲了杯速溶咖啡,徐徐的热气似乎慢慢与周遭的冷空气打成了平手,身体里各个细胞也逐渐活跃起来。
从小到大,一直都在母亲身边,可这几年从高中毕业再到在另一个城市开始读书发展,才渐渐发觉有些距离是伴随着成长必不可少的遗憾。有些思念,渺渺如烟却又丝丝缠绕在记忆碎片上。
记得大学假期第一次回家,不巧碰上阴雨绵绵,但因为心里那份雀跃的欣喜,雨也随之有了不一样的欢愉。抬头望着雾蒙蒙的天,千万雨点齐刷刷地落下,天地之间成了雨归家的通途。这么想来,我竟然和雨有着同样的情愫,心间就更不觉冷意了。打开家门还未开口,母亲第一句话便问我有没有被冻着。笑意和暖意萦绕在母亲的脸上,更摇曳在我的心底。一股久违的家的气息重新将我呵护起来,像春日下午的暖阳般温煦。
踏进房门,放下行李,还没来得及脱下外套,母亲便指着厨房说正给我热着奶汤蒲菜。一听到“奶汤蒲菜”,以往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济南名吃有很多,我从小最喜爱的便是这道奶汤蒲菜。母亲是个心思极细的人,为了能有最新鲜的蒲菜,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在邻近郊区的塘子边,会有老伯清晨摆摊儿卖蒲菜,而且还是刚从塘里拔上来的蒲菜,清鲜嫩脆。
一到周末,母亲起得比工作日还要早,换上轻便的运动鞋,拎起一个长长的布袋便出发了。塘子位置实在太偏远,母亲辗转几趟公交车,最后又走了两三公里的土路才到达目的地,那时已近9点了。母亲拎着买好的新鲜蒲菜,来不及歇脚,又原路返回家。刚睡醒的我看到门口风尘仆仆的母亲,一脚的黄泥,滴着水的布袋,风吹得微乱的发,还有额头上密涔涔的汗珠。我问母亲去了哪里,她一句诉苦都没有,举起一簇青绿的蒲菜,笑着说买到了很新鲜的蒲菜,要给我做爱吃的奶汤蒲菜。一瞬间,我仿佛被母亲脸上的那股骄傲和期待给击中了——好像有一份炙热的光从母亲身上散发出来,尽管此刻的她略显狼狈。
我一步上前接过母亲手里的布袋,毛遂自荐要帮她一起做这道奶汤蒲菜。母亲依旧笑了笑,将布袋递给我。开始剥蒲菜了,母亲坐在我旁边,手把手教我如何择掉老叶,最后留下的嫩心,口感最佳。很快,在母亲的教导下,我对剥叶流程熟络起来。不一会儿便有了一整盘的嫩蒲菜心。母亲将嫩心切成小段,浸泡过后用沸水焯过。锅内油热后,母亲先将葱白姜丝炒出香,加入适量清水,又舀了一勺面粉放入烧热的水中,汤色渐渐变成了奶白。母亲看了看火候,又掂量了汤色,转身将提前切制好的冬菇、玉兰片、火腿都倒入锅中,最后加了母亲特别准备的葱椒绍酒,焖烧起来。我已经隐隐闻到香气了,赶紧踮起脚想要望一望。母亲为了舒缓我的迫不及待,讲起了臧克家《家乡菜味》里的蒲菜:“大明湖里,荷花中间,有不少蒲菜,挺着嫩绿的身子……”又讲到了她清晨走近塘子时看到的那一丛丛蓬茸的蒲笋,映在微红的日轮下,像极了一幅诗中的画。可是只顾看景色,一脚踏进了泥坑……说到这里,母亲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下次可得好好看路喽。”
终于,汤熬好了。母亲小心地盛入瓷碗,端放在餐桌上,招呼我赶紧过来尝尝。奶白色的汤汁,蒲菜浸润其中,嫩白中透着浅浅的绿意。一口奶汤,一口蒲菜,再夹片喷香入味的火腿,配着嫩滑的香菇和玉兰片,这种味蕾上的享受实在无法言说。我想让母亲快来尝尝这份鲜香,一抬头,看见她正笑吟吟地坐在我面前,带着满足的神情望着捧住汤碗难以释手的我。眼神中还闪烁着一份骄傲,如同早上她带回新鲜蒲菜时一样的骄傲。
从家庭到大学校园,在新鲜和挑战中度过了太多的日日夜夜,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那份在外闯荡的勇气是来自哪里。现在的我,明白了这份勇气的来源:母亲,正是我内心深处最温暖而铿锵的力量,在人生的旅途上熠熠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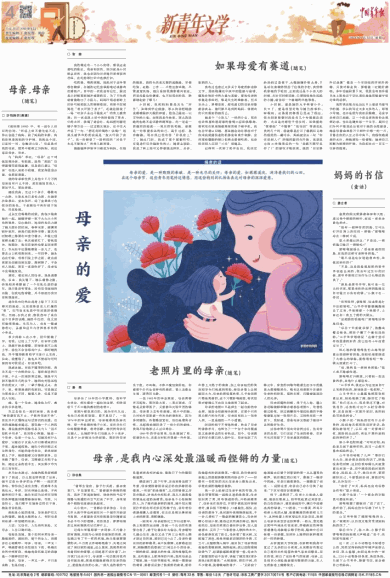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