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嘴边有一个小小的痣,都说这是爱吃的象征,我是相信的,因为就连小时候去诊所,我也会因为讨厌嘴巴里停留的苦味,在吃药和打针中选择打针。
吃药难,喂药更难。妈妈对于这件事怨念颇深,在她的记忆里深刻地记录着两次滑铁卢。其中的一次我没有记忆,据说是小时候看到她冲感冒药后,为了不吃药就偷偷跑出了小院儿。妈妈吓得追到街上时恰巧被前院儿的婶婶看到,结果不仅被冤枉“发火吓到了孩子”,还被迫接受了一场“对孩子永远不能发火”的育儿教育课;另一次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得了胃炎,中药太苦,我喝了就会吐,妈妈把吃糖吃橘子等方法一一试过都无效后,忍不住大声说了一句:“药还有好喝的?快喝!”结果又被爷爷奶奶说成是“发火吓到了孩子”,再一次接受了一场相同的“对孩子永远不能发火”的育儿教育课。
她磕磕绊绊地学习着成为妈妈,在她的眼里,我的生活是无数的起跑线,学着吃饭、走路、上学……不管出发早晚,不管速度快慢,她只是陪我摸索着向前走。若是母爱也有赛道,也不知现在的我,陪着她走到了哪儿?
小时候,我和妈妈像是天生“对手”。如果我学过画画,那么我会把她画成瞪着铜铃大眼的钟馗,把自己画成一只可怜的小鬼;如果我是作曲家,那么我送她的也绝不是恬静的钢琴曲,而一定是一首激烈的摇滚……现在的我和她,更像是一对相爱相杀的知己,高手过招,各有输赢。现在我已经有些“后浪居上”了,她出门时,我成了那个絮絮叨叨、反复进行反诈骗宣传的人;她要去医院,我成了网上挂号又带着她去排队、分诊、取药的人。
我听过也看过太多关于母爱的影音和文字,那些隐藏在平淡中的重感与温情,爆发在转折中的力量与柔韧,那些母亲的形象是相似的,像是天生的奉献者。但书本合上、屏幕变黑,那些虚幻的母亲形象就会淡去,她们都不是我的妈妈,我拥有的只有眼前的她而已。
她是个“小孩儿”一样的少女,现在也依然喜欢看甜甜的爱情小说和偶像剧,喜欢宅在家里围着厚厚的被子刷手机。我也在学着认识她,原来她会站在那些对于我来说便捷快速的机器前面束手束脚,会用那些蹩脚的借口拒绝去看病吃药,也会轻信别人买回“三无”保健品。
记得有一次领了奖学金后,我决定给妈妈买条裙子,大概她嫌价格太贵,于是站在身侧悄悄拉了拉我的手肘,我悄悄抓紧她的手轻拍,正如我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无论何时想回家,只要悄悄抱住妈妈的小腿,就会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我。
小时候,爱是她的大手牵着小手;长大了,爱是我坚定地与她五指相扣。转眼间,这条爱的赛程已经走了很远。现在回家聚餐时我是有几个专属禁忌词的,尤其是对着侄子侄女时,如果提到“惯着他”“不懂事”“我当时”等诸如此类的几个词,那就像是打开了暴晒后又剧烈摇晃的一罐可乐,妈妈就会从一句“你还说别人?”的强烈疑问句开始,直到说出我20件糗事后的一句“我都不稀罕说你了!”的感叹才能结束。她的“历史事件记录簿”像是一个可回收的环保炸药桶,只要对象是我,那能量一定随时满格。多年经验积累下来,我甚至有些怀疑书本上那些关于记忆遗忘曲线和能量守恒定律的说明。
我的表达能力远远比不上爱读书爱写字的她,所以我写过太多太多的人,却很少写她。也许是因为我依旧稚嫩,还没学会将自己抽离,以一个旁边者的身份去观察记录;也许是嫌弃每一个文字,疑问它们为何不能表达出我对于她的全部感受。她是母爱森林里万千树叶中唯一的一片,甘愿在我的人生之书中风干。我吸收她青春的水分,给她增加一些褶皱;她将自己拆解为细密的纤维,为我织补出一页又一页新的篇章。
张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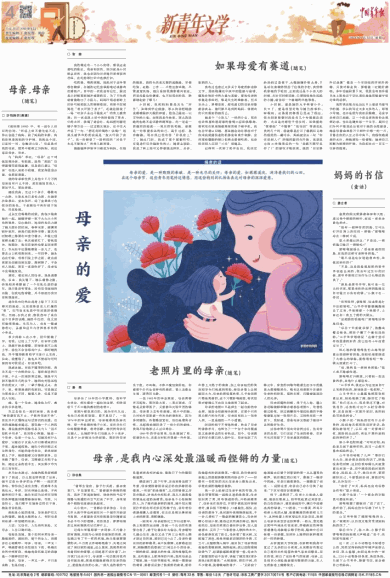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