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进入故宫工作。
我们部门的办公地点,坐落在故宫的西南角,曾经这个地方叫“南大库”,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原是一处库房,用于存放灯笼等。虽然现在的建筑是后建,但还是很“古老”。比如我们办公室除了空调、电脑、打印机,再没有别的电器,喝水都是提着水壶去水房接。防火对于故宫来说太重要了。
刚工作那会儿,我周边的同学、朋友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在故宫做什么工作,英语讲解员吗?”可见当时大家对博物馆的认知不足。但现在,身边人问的都是故宫最近有什么展览、出什么书了,有没有课程可以参与。这种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博物馆近年的蓬勃发展。
我能“进宫”,很大程度上,与一个机构有关。
2013年,国际博协、中国博协和故宫博物院正在合作筹建国际博协培训中心,由故宫博物院运营管理,办公室就设在我所在的宣教部。我也在同年进入故宫工作,可以说是和培训中心一同成长起来的。
国际培训让我的英语专业有了用武之地。培训中心每年举办两期常规培训班,主题涉及博物馆管理、教育、藏品、展览,以及博物馆当下热点话题。
上个月,我们刚刚办完今年的春季班,一位国外专家问我,为什么中国要建立一个国际博协的培训中心,并在10年里给予持续的资源和资金支持。
我说,因为我们非常看重这个项目的价值。那价值在哪里?
可能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回答。但我想起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最近的两期培训,都有学员作为授课专家回归。曾经的学员,经过10年的积累,已成长为一馆之长或大学教授,用自己的所学反哺培训项目。当然,这不全是培训中心的功劳,但培训中心的确打造了一个国际博物馆人能力建设的平台,培养了未来的管理者。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学员们可以相互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分享疑惑困难,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同时也能够相互了解,开拓思维,开阔眼界。
第二件事,就在前几天,一位博物馆同行咨询能否帮忙联络韩国某家博物馆,他们想去参观交流。这种咨询,我收到过很多,大多是希望通过培训中心,与国外博物馆建立联络,谋求合作。而他们之所以会找到我,是因为经过10年的发展,培训中心构建起了一个囊括85个国家500多位国际博物馆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网络。这个网络不仅让他们因共同的培训经历而拉近距离,也为博物馆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储备了人才。国际博协、中国博协和故宫博物院也都希望这个网络,能够促进博物馆国际交往与合作。
参与培训中心工作的过程,也是我个人能力不断成长的过程。
在组织培训的过程中,我的国际交往、统筹协调和应对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我有幸在国际博协大会上,代表培训中心发言,向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同行展现中国博物馆的实力与活动。
作为博物馆教育人员,培训课程对于我做好博物馆教育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在培训期间接触到国内外博物馆先进的资讯、理念和案例。这些年,我做教育课程开发、图书出版、短视频运营,很多理念和想法都源于培训课程的启发。
2017年,我带着自己开发的课程《康熙与西学》,在悉尼的中国文化中心给孩子们进行全英文授课。我想告诉悉尼的孩子们,在很久以前,中国就已经和西方有了文化往来,现在我们依然延续着这种往来,正是这种往来让我们彼此了解、建立信任。
我也将自己组织培训的经验和思考以论文的形式分享出来,希望为大家组织和申报国际培训项目提供借鉴。
未来,我也将继续提升自己的专业积累,提高自己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汲取国际营养,推动中国博物馆走向世界,让中国声音更加响亮。
姜倩倩 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教育培训组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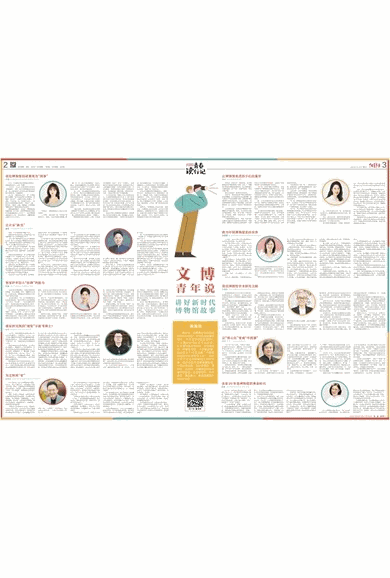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