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硕博的研究方向分别为先秦文学、楚国历史文化、石器时代,与荆楚文化的主要内容及湖北省博物馆的藏品体系基本是匹配的。
我从事的工作涉及博物馆的学术和教育两个环节。简单来说,我们做学术研究,就是通过我们的学术能力,把晦涩难懂的考古报告、研究资料等“翻译”出来。
这是我们藏品保管的基础,是我们陈列展览的基础,是我们社会教育的基础,当然,也是我们跟观众交往交流的基础。
“翻译”出来之后,还要进行“阐释”——将“翻译”过来的学术观点,展示给观众,包括信息化的展示,或是提供教育活动等。
我本科学中文,喜欢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特别是《楚辞》《诗经》,到现在,我在家里也偶尔吟诵一段,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能背《离骚》。
但像这些文学作品,如果你不了解楚国历史,觉得还是有点虚。我们是师范类院校,本科毕业之后,我没有拿着教师资格证去学校当老师,而是选择去读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慢慢完成从文学到历史学角度的转型。
在我看来,考古本身是个很有个性的专业。因为每年它都有很多新的发现、新的材料,不停地给人惊喜。而且做考古发掘,就像“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墓坑里能挖掘出来些什么。
进入博物馆工作也是偶然的机会。当然,每一次偶然背后关联着一系列的必然。
2010年,我研究生毕业,当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资料室想招一名图书管理员。我的导师跟我说,考古所资料室的考古发掘报告比学校资料室的还多,到那里可以尽情读书。然后我就很开心地去了。但是报到之后,单位可能觉得一个研究生去当图书管理员可能有点浪费,就给我调换了3次岗位。
我在博物馆办公室待了5年,主要负责新媒体以及宣传方面的工作,并承担了博物馆一些重要稿件的撰写。这个时段也是我思考、践行学术应该如何通俗表达的开始,与此同时,也是我思考、践行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应该如何与我们的观众打成一片的开始。
信息中心的8年,我主持了湖北省博物馆的智慧博物馆建设。虽然我不是计算机专业出身,但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专业背景给了我们很强的支撑。这个信息化的产品做成什么样子,只是一个形式,对内容的理解、延伸需要专业的支撑。
在信息中心,我有机会去探索如何在展览之余,把我们的文物、我们的展览通过信息化手段去建立关联,然后通俗表达。
2012年,我担任中央电视台大型历史文化专题片《楚国八百年》的文史统筹。2018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楚文化符号系统的提炼与考察》。
我们做信息化工作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展览只能在规模上做大,如何把这些文物连成一个展览体系,将一个完整性的故事讲给观众听?
我希望观众来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以后,不是只记住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这些明星文物,而是通过馆方努力,把湖北省博物馆的馆藏资源当成一个整体,把荆楚文化当成一个整体讲给观众听。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做的,是努力向观众呈现某一支地域文化的生老病死,文物背后的喜怒哀乐,进而“品”出一些诗意来。
张謇先生有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在湖北省博物馆建馆 70周年之际,在湖北省博物馆发布《湖北省博物馆三年发展计划(2023-2025年)》的关键节点我愿再接再厉,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湖北省博物馆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尽绵薄之力。
杨理胜 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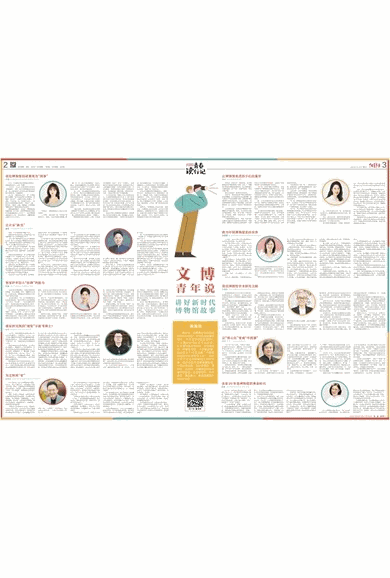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