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楼上跃下的那一刻,我突然想知道,为什么猫从7楼掉下去不会摔死。
再睁开眼时,我发现自己在一个笼子里。
“我被绑架啦?!”正要发出歇斯底里的惊叫,我却听见了周围此起彼伏的嘈杂声。正想坐起来一看究竟,却发现我的手本能地把我的身体撑起来——往下一看,我的双手竟然变成了毛茸茸的爪子。
“什么鬼?”我难以置信地一遍遍查看我的四肢以及比脑袋宽的胡子,还有身上灰白的绒毛。
“变形记吗?”我大声说话的时候,笼子外的人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发出的声音是寻常的猫叫——我的的确确变成了一只猫。
我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心理建设——以前我就时常羡慕宠物猫,可以过着简直如神仙一般的日子。不管如今是不是梦,都比当苦命人好多了。
突然,门被打开了,一双大手伸进来把我抱了出去。
“你的猫治好了,可以出院了。”我抬头看了眼说话的医生,是一位中年大叔,又看见一个神色忧郁的年轻小伙子,黑色T恤,沉重的黑框眼镜,瘦瘦小小的,伸手把我抱过去。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似曾相识,我脑子开始嗡嗡作响,但我的注意力很快被医生和小伙的谈话吸引过去。
“这只猫挺厉害的,从那么高摔下来都不死。”
“这是我奶奶乡下养的猫,平时老鼠抓得多,可能比较壮实。”
我吓得一哆嗦,心下暗道可恶,我平时最怕老鼠了。
就这样,我跟着忧郁青年回到了他的家里。房子是他跟奶奶一直住的老房子,装修非常接地气,摆设也主打质朴实用,只有入门时映入眼帘的蒲公英水彩画与房间的气质格格不入。
浅蓝色的背景下是飘扬的白色蒲公英,颜料应该混入了特殊物质,使得蒲公英在阴暗中是普通的白色,在阳光下却会映出光晕。画被金色的边框装裱起来,看起来像是别人送的礼物。这幅画在这个家里像是沙漠里的一股清泉,美好得不像这个房间的物件,更像是苦涩生活中的一个幻象。每当阳光照进屋子里,画上的蒲公英就像换了一副面貌,变得生机勃勃。我很喜欢这幅画,经常趴在客厅里看着它。这幅画好似有一种魔力,要把我带入某种思维的漩涡。它热烈奔放、积极阳光,但它沉默不语,只静静地与我对视。
然而我更在乎的是,我发现我的“猫生”(谁让我现在是猫呢)也过得比较困窘。忧郁小伙儿叫王乐,上个月刚被裁员,从小只有奶奶带着他,上个月奶奶也去世了。他砸锅卖铁也要治好我,因为我算是他唯一的感情寄托了。他经常会对着我说话,给我喂吃的(刚好我也不敢抓老鼠),开心的时候会撸我,不开心的时候就对着我一言不发。这种状态我很熟悉,多少已经带点抑郁了。虽然没有穿越成“富二代猫”,但作为一只猫,我再也不用面对失业失亲,还欠了一屁股债的窘境,已经非常幸福了。
但王乐轻松不了。为了给奶奶治病,他也欠了一屁股债。上门的债主是他爸爸的老朋友,虽然态度已经很好,不忍心逼迫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但是也把“还钱”两个字刻在脑门了。王乐是个实心眼,脸皮也薄,人家只说了两三句,他就开始一个劲道歉,说到最后债主看实在是很难要回来钱,只能走了。王乐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清点着手头的欠条,随即陷入一种专注的沉默,对着窗台发呆。他还疯狂地投简历,反反复复面试,有些起色但也不大。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某个明媚的清晨,他把印好的一大堆简历全扔了。
我渐渐发现王乐的抑郁有恶化的倾向。邻居古奶奶偶尔会来看王乐,劝他振作起来,说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王乐越听越沉默,我也越听越难受。我的心有种被“背刺”的隐痛,身为一只猫,我依然会对人类的痛苦产生共鸣。我看见王乐脸上的皱眉慢慢展开,双眼的焦虑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所谓的冷漠,以前他的神情是落寞的,现在他的眼睛像一潭死水。
某几天我开始做梦。梦见王乐死了,我成了流浪猫,最后在某个垃圾桶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然后结束“猫生”。我吓出一身冷汗,决定还是要把主人留住。
我开始每天都缠着他,用我的存在让他想起他奶奶,让他留恋人间。这些天都是晴天,蒲公英每天都闪闪发光,倒像是嘲讽它的主人的日子黯淡无光。王乐或许也有这种感觉,一反常态选择在大晴天时把窗帘拉上,但他从来不会把画挪走。
他现在整天不出门,可以在家里躺一天,但精神却像紧绷的弦。我发愁得很。我开始上蹿下跳闹事,让他不能忽视我的存在。他最近走神的次数越来越多,还经常忘记给我喂吃的。他身上绝望的气息越来越沉重,满脸写着“生人勿近”。古奶奶常会过来给他送点好吃的,顺便安慰几句:“你奶奶也不希望看见你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我注意到,每次她说的时候,王乐脸上的表情就更冷漠了。
看着王乐的样子,一种熟悉的痛苦爬上心头刺激我。我知道王乐的感受,那是一种像在深海里溺水的感觉,让你连自救的勇气都没有。
王乐又忘了给我喂饭。我不得不开始翻箱倒柜地闹事,以吸引他的注意。在杂物间的一个小角落里,我翻出来一个铁盒子,里面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我用脏兮兮的猫爪子把它翻开,第一页是几个大字:“乐乐一岁。”然后是几张小孩子和大人的照片。我接着往下翻,翻到了王乐爸爸的照片。接下来的几页是几张报纸上剪下来的纸片,原来王乐的爸爸为了在火场救小朋友,自己却牺牲了。
“乐乐5岁,会画水彩画啦!”后面有署名,却被蓝色的水彩笔重重涂掉了。
我这才发现,铁盒子旁边有一堆装裱起来的栩栩如生的水彩画,即便布满灰尘也不难看出精心勾勒的笔触。铁盒子底下压着一堆蒙尘的证书,应该是王乐小时候绘画比赛获奖得来的。我猛然意识到,客厅那幅蒲公英,原来是王乐的获奖作品。那叠证书,最大的一本是全国比赛的证书。猫咪的好奇心真的很重,我急于证明我的猜想,于是艰难地把它翻开,获奖作品正是叫《烈日下的蒲公英》。
“我以后再也不画画了。我要考上好大学让奶奶过上好日子。——我的17岁愿望 王乐。”这是相册最后一页上的内容。我敏感地察觉到,这本相册没有出现过与妈妈相关的内容。我不知道他在17岁这年经历了什么,也许他过完17岁生日之后,就再也没有翻过这本相册了。但我知道,他对这本相册的每个细节肯定都了然于胸。
我翻完了整本相册之后,发现相册最后一页的背面居然有奶奶写给王乐的话。“乐乐,生活总是不尽如人意。不要总为了奶奶委屈自己,你要享受你的人生,像你画的蒲公英一样活着,去自由飞翔吧。”
我的猫爪子把纸面抓得皱巴巴的,画里蒲公英的样子,阴天下蛰伏沉默,实际上给点阳光就灿烂,多自由散漫,多好养活,也许这就是王乐的期待吧。我想奶奶的话应该让王乐看见,咬着这个本子就往外跑。
突然,我听见客厅传来清脆的玻璃破碎的声音。我放下拖到半路的本子先飞奔出去,看见王乐跪在地上,对着一堆玻璃碴子哭泣。他的画掉了下来,画框碎了,他止不住地流泪,抽泣着。我跑到他身边,看见画的纸面露了出来,上面有血迹,王乐的手被割破了。
“结束了,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突然停止了哭泣,开始喃喃自语。
阳光正从窗台洒进来,染上血色的蒲公英在烈日下暴晒,那株蒲公英仿佛在流血。
蒲公英闪烁的美丽光晕和血迹的鲜红同时出现在一幅画上,仿佛代表生命的两种极端状态在对峙。 我的脑袋又开始嗡嗡作响,画框已碎,王乐的心也跟着碎了。
突然间电脑响了一声,王乐却无心顾及。我跑过去瞄了一眼,只看见了提示框的几行字:“恭喜!您已被我司……”我猜想这是新工作有着落了,跑去他周围又蹦又跳、大喊大叫,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直接站起来,径直走向了窗台。
王乐爬上窗台的那一刻,我用了我最大的速度冲上去,死死地咬住他的裤腿,我只恨我不是一条狗——狗的力气能大点。
他低头看我,摸了下我的头,眼泪流了出来:“很遗憾我不能照顾你了。”
我大声地吼道:“谁要你照顾了,你先照顾你自己!”但是,他听见的只有“喵喵喵”。
他哽咽道:“上次你从楼上摔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很害怕?”
“你别扯这个,看你的邮箱!你新工作有希望了!还有你爸爸,他是个英雄,他会怎么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奶奶出事的时候,我没接到她的电话。”他平静地说,“我没见到她最后一面。我过成这个鬼样子,真是不给她争气。”
我急死了:“奶奶不是这样说的!你自己去看!”我试图用亲情来挽回他,可惜他不可能听得懂。
“你想劝我吗?”他低下头温柔地看着我,眼泪滴到了我的头上,“我也很想继续陪你。”
我继续“喵喵喵”地叫着,试图让他到桌子那边去。
“人生为什么会这么艰难?”
“你找到工作了,不艰难了!你借的那些钱都是跟熟人借的,慢慢还就行!路子多的是,别急嘛!”我还是在“喵喵喵”地喊着。
“我跟古奶奶说了,把你送给她,她很喜欢你。”他摸着我的头冲着我笑,对我作最后的告别。
王乐一只脚已经迈了出去,可是很明显,他还在犹豫。在他犹豫的几秒钟里,他转过头来,我们四目相对。那一瞬间我的脑子又开始嗡嗡作响,这张脸、这双眼、这些伤心的泪水,变成裹挟着情感巨流的记忆向我奔袭而来,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一个人。王乐不看我了,他看向窗外,此时窗外的街道驶过一辆垃圾车,环卫工人正在清理垃圾,他依次把楼下的垃圾桶全部清理完,然后离开了这条街道。我的脑子闪过了无数画面,突然间我看见王乐的脸变成了我的脸,阳光下我的脸憋得通红。我有一种趋于本能的直觉,王乐不是在等环卫工离开,他是在等我。
我脑子已经发热了,使出全身劲儿,趁他身体不平衡时猛地把他撞回去,但我却被弹了出来——
我又从7楼掉了下去。从楼上跃下那一刻,我突然怀疑,猫从7楼掉下去是不是真的不会摔死。
再度睁开眼时,眼前只有白茫茫一片。但是白茫茫的视野中间,有一个像公司前台一样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像秘书一样的中年男人。
“咦?怎么这么像《重启人生》”?
他热情地冲我打了招呼:“恭喜您完成心愿,现在可以前往下一趟旅程了。”
“我有什么心愿?”
“哦,您上次来这的记忆可能被清洗了。您于3月6日下午来到这里,由于前世是个好人,所以拥有一次完成心愿的机会。”
好家伙,真的是重启人生。
“那之前我的心愿是什么?”
“您那时候希望成为一只猫,这样从7楼掉下去就不会死。”
“所以我短暂地当了几个月的猫?”
“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让你成为猫,其他的情况都是随机的。”
“那我现在还能许愿吗?”
“不可以了。”
“王乐被我救回来了吗?”
“他没事了。”
我松了一口气,他得好好活着。
“那我能不能回到上一世啊?”我知道希望不大,但还是试探性地问。
“技术上来说可以的。因为你的身体还活着,你现在算是灵魂出窍了。回去就行。”
“啊?”
“就是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什么代价?”
“您下一世会是首富之子,您选择回去的话,可能就是普通人家了。”
“那没关系,我要回去。”我还没跟奶奶打招呼就走了,我真的太冲动了,无论如何都要回去。
“那你闭上眼睛。”
我闭上了眼睛。
张杏(27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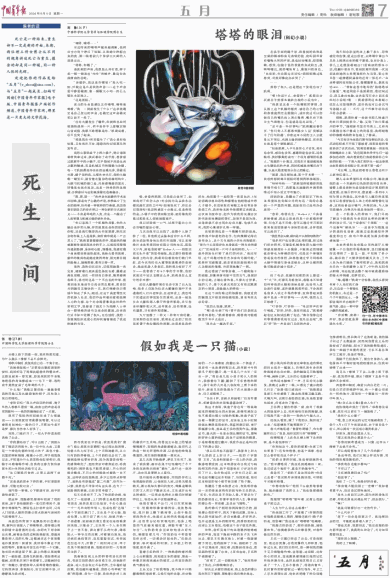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