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小院,那只叫乌云覆雪的母猫和它的儿子小云,都会从附近院子穿过栏杆钻出来,迎候我们。有一次在小区靠近我家的路上,车灯照亮了母子俩,它们躲进路边的灌木丛里,我赶紧停车下来,喊:乌云,是我啊。它们听出了声音,闻到了气味,跟着车子回到了家。我停好车,回家收拾一下,出门一看,乌云覆雪坐在我的车顶上,悠闲地舔着前爪。我想,它记住了,这是我的车,它也有份。
我每周来一次院子,走的时候,留足一周的猫粮和干净的水。有时吃得干干净净,有时还会留一点。如果只是乌云覆雪母子吃,它们会留一点,像人过日子一样,总要考虑下一顿;如果吃得干干净净,一定是有其他的流浪猫来偷食——流浪汉只关心眼前的一顿。
快一年了,我已经把它们当作“院猫”养,给它们上了“户口”,登记了“粮本”,定期打疫苗,定时买猫粮。我来时,它在地上打滚,露出肚皮,用鼻头和两腮使劲蹭我的手。走时,透过车窗跟它们说再见,母子俩立定看我,眼神有点忧伤;有时假装没看见我,到麦冬丛里和几只青皮小癞蛤蟆玩。
昨天我到院子里,没看见它们,今天仍然没见。流浪猫的命运很难预测,我将它们视作“院猫”,但我并不天天住在这里,它们也在多家院子之间逡巡。小区里大多数人对流浪猫心怀善意,但小区里车子开得很快,各种意想不到的伤害时时存在,能活下来,并不容易。心里闪过这样的念头,嘴里赶紧“呸呸呸”。
傍晚,小云回来了。赶紧问它,你妈呢?它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不怎么理我,从栏杆里溜走了。这小东西。
去年秋天,乌云覆雪带着孩子光临寒舍。冬天,我给它们母子在背风的一丛竹子下搭了一个窝。下雪天,乌云覆雪冻出了鼻涕,我给它买来猫咪专用电热毯,它终日在毯子上“打坐”,很快感冒就好了。小云不到一岁,正贪玩,我在爬藤铁架上用细绳吊了一只塑料小鸟,它跳着抓小鸟,腾挪跌宕,能将小小的身体翻出许多花样。
再来时,小云前腿瘸了。小猫为求关注,有时装瘸,我以为小云逗我玩,没太理会。我从家里远远看它,还是瘸着,它没有必要表演给无人的空地看。我抓住它,发现前腿肿了,化脓了。二话不说,送宠物医院。医生手脚麻利,给它挤脓。“……”我无法用拟声词模拟它的叫声,从未听见一只小猫发出那样凄厉的声音,小云太嫩了。这样太疼了,我赶紧让医生停下来。医生说,可以先打麻药再清创,不过,打麻药要加300块钱。
唉,你怎么不问就挤呢,加吧,加吧,赶紧先打麻药。
医生轻车熟路,清创、上药、包扎,包扎好的前腿让小云看上去像拿了一根火腿肠。我又请医生给它驱虫,打疫苗。小云醒过来第一件事,是想褪掉这个火腿肠,我只有给它戴上脖圈,带到家里养几天。
我的电脑屏保是一组小奶猫的动图,小云三下两下跳上桌子,看到屏幕上的猫,它将那只未受伤的脚伸到屏幕后去勾,然后眼睛盯着屏幕上的几只猫。它真聪明,我家里养了10年的猫连镜子都不会照,它居然能看屏幕。
那一段时间正好放假,我让小云在家里住了几天,一直到伤口基本恢复。那些晚上,它睡在我床上,却爬高上低,一刻不停。医生说包扎太紧,会压迫血脉;松一点,很快脱落。为了安全,只能松一点,不断起床,为它重新包扎、固定。
我一边包扎一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伤害它?看伤口,不像。回来后我在院子里东看西看,发现爬藤铁架下面的一个横档锈烂、断开了,变成了尖锐的铁刺。小云可能往上跳跃抓小鸟,落下时前腿正好扎到铁刺上去了,这是我未曾料到的。我找来一节废弃的方形钢管,套上去,清除隐患,这才放心。
小云腿好了,总提防我,罐头照吃,走近它,立即跑开,看来手术还是给它留下了很大的阴影。乌云覆雪随时随地都会打滚,只要见到我,就跑过来,脑袋蹭过来蹭过去。
今年春天雨水多的时候,它们晚上还待在窝里,我在窝前加了一个透明的塑料布,挡风雨不挡视线,白天还能洒进一缕阳光。夏天来了,哪里都是玩耍休息的地方,就不再进窝。趁天气晴好,我将窝里的毛毯、绒布、毛巾,还有地垫,都拿出来清洗。不敢用肥皂和洗涤剂,一则不能给这些东西染上化学的芬芳,二则必须保留原来的气味,它们才感到安全。只能用清水洗去浮尘,多搓几遍,在紫藤架上晒。晒干后,我将原来的基座垫高,再将地垫、毛巾一一放进去,心想,等秋风凉时,它们会回来的。
没想到这几天,乌云覆雪不见了。
我将新买的罐头打开,以为它俩闻到味道就会回来。不时出门看看,罐头吃掉了一半,是另一只白猫吃的,它特别胆小,瘦弱不堪,见人就躲,很难与人类建立感情。
乌云覆雪不是这样,它第一次见到我就贴着裤腿绕踝三匝,不忍离去。
我向别人介绍乌云覆雪,都会说它脾气好,知进退,有眼色。前一段时间,我在室内的沙发上午休,沙发放在大玻璃窗下,窗外我随便放了两把椅子,睡醒一抬头,发现窗外椅子上,乌云覆雪也在酣睡。隔着一层玻璃,我喊它,它醒来,马上就在椅子上打滚,应和我的呼唤。
它知道自己是流浪猫,不过分撒娇,不随便进屋,只在门口盘桓。给它罐头,吃两口,就留给儿子吃。一只跟小云花色一样的公猫来,它就站在一旁看着公猫吃,好几次后我才反应过来,这是小云的亲爹。乌云覆雪凭着一己之力打下江山,全家共享福利,真是一只懂事、体贴的好猫。
它上哪去了呢?我清扫院子里的落叶时在想,坐在房间里看书时也在想。接连多天,毫无音信。
我以为这种温暖的关系能持久,每次来都怀着期盼,我尽情享受乌云覆雪给我带来的快乐。但我没有一直陪伴它们,也许,在它最需要我的时候,这扇门锁住了。
突然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多情女性的那篇著名作品,痴情女子对她默默爱了一生的男人说:我对你的爱,像你手表上的指针,分分秒秒,我的心为你跳动,从不止息;你一天之中,有几次看一下手表呢?
小时候看这篇小说,如遭电击。女子炽烈的情感像一道刺眼的亮光,照彻了我空茫寂寥的内心。年岁大了,慢慢想,世上竟有这样的女子,将微弱的感情燃烧成漫天大火,最后将自己的一生放在大火里焚毁;男子根本就不认识她,女子只是他一生无数风流韵事里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色,她会为了那一丁点情感的蜜糖,尝尽一世的苦楚?这是不是男性作家的狂想?不用这样吧,这世上有真命天子需要一生守候吗?
小说在探索人性的各种可能,我未曾经历、也未曾发现的情感模式,茨威格写出这样的故事,自然有他的道理。
提防我的小云还时来探望,而乌云覆雪决绝消失,想到这,我总有些不甘。
我盯着小云的脚步,看到它往离我家不远的院子跑,那里铺了雪白的鹅卵石,还有喷泉、假山、高高低低的小木屋,石头做的小鸟、小鹿,还有温柔和善、刚退休的女主人。如果乌云覆雪到她家去了,找到了更好的“粮本”,上了附加值更高的“户口”,我是不是能彻底放下?
从这家的前院找到后院,没有乌云覆雪的影子。乌云覆雪,你的心真硬啊。
我也设想过乌云覆雪独守我院子的场景,百无聊赖待在紧锁的大门前,有时一个星期都没有人的气息,只有老癞蛤蟆的两个小儿子,皮肤有点青绿色的小癞蛤蟆,在栏杆边的麦冬丛里跳跃,让这个院子有点生气。香樟树杪,竹子梢头,常有小鸟驻足,但那也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它够不着,猫一攀爬,鸟就飞走了。
如果有人天天呼唤它,为它梳毛,给它准备好吃的罐头,它能在那个人的脚边打滚,在那个人的怀里打呼噜,有限的猫生,是不是更充实更快乐一点?
它曾经跑到小区门口迎接我的车子,曾经看到车灯,就从旁边的院子里赶紧跑过来,见到我,就滚在地上露出肚皮,对我如此信赖,如此依恋。我以为这是理所当然应享受的待遇,就得之不珍惜。我让它的希望常常落空,现在,是我接受惩罚的时候。
一声喵呜,拨动心弦,那时我的心硬一点不去理会,就没有开始——它永远是一只与我无关的流浪猫。它的存在与消失,它到谁家成为宠物猫,都跟我没有丝毫关系。
我最初是怎么与乌云覆雪对上眼的,已经想不起来了。一旦建立联系,人心啊,“没有个见好就收的”。
冯渊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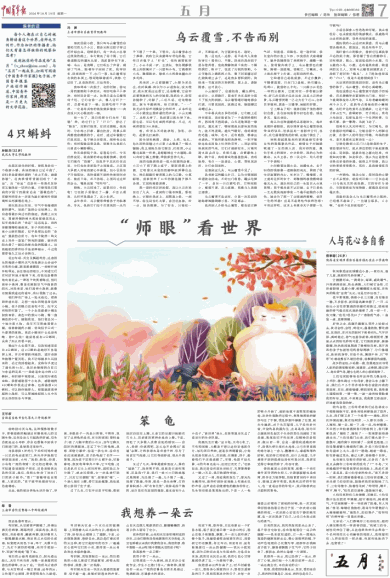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