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爬着梯子,登上房顶,开始拍照。好不容易回趟老家,当然要大肆在朋友圈炫耀下城里人感受不到的风光,比如,屋顶上晒着的东西,我发到朋友圈里问,谁知道这是什么吗?
那是红薯片。用一种特殊的模具,把红薯削成数毫米厚的薄片,放阳光下晾晒,三四天后,水分蒸发,只剩干脆的躯体。平时熬粥,可放上数片,干脆的红薯片在粥里重新变得绵软,却又不会像新鲜红薯一样被熬烂,口感极好。
一个跟着父母远离老家到成都做生意的朋友很快回复我:“红薯片,我娘可爱吃了。”我回他:留个地址,我给你寄过去,让老人家尝尝鲜。
我极能理解老人的这种爱好。虽然离乡数年,依然忘不了曾经用来果腹的食物。我的父母也是如此,以前每年都会种红薯,后来不种了,但每年秋冬都会买下很多,偶尔就会擦成红薯片,晒干来吃。胃的记忆,比头脑要好很多。不只是胃,牙齿咀嚼的软硬,舌头上味蕾的感觉,甚至是下咽时与食道的摩擦感,都会令人怀念。
老家亲戚到现在,都爱吃一种叫做“苦累”的东西。听名字,就能猜出,那不是什么美味。到春天时,榆树上长满榆钱(榆树种子),人们便采下来,放锅里煮煮,捞出后,放进玉米面,稍微洒水,搅拌均匀,再放蒸屉上蒸熟。出锅后,用筷子挑一块放嘴里,一定不好吃,口感也差,能清楚感觉到玉米面的颗粒感从口腔传到食道落进胃里。吃得口大了,还可能被噎一下。
古书上说榆钱“久食令人身轻不饥”,确实如此。这种又称为榆钱饭的食物,就是饥荒年代传下来的。但这两年到春夏之交,父辈们又开始做来吃。吃得当然不是美食,而是回忆。
几乎每个长假,我都要回老家。我跟老婆说,那是我精神上的根系所在。但其实,也是因为胃的召唤。之前看过阿城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胃是故乡的蛋白酶,人们之所以思乡,其实是思饮食,思吃的氛围和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全是这种蛋白酶作怪。
信然。
回到家里,父亲买来了鱼和鸡,我却一概没有兴趣,只想吃饺子、炒面、红薯饭。都是小时候常吃的东西。甚至小时候不爱吃的面条(有段时间,父母以制作面条谋生,这也就成为家里的主要食物),现在都觉得别有一番味道。美食家蔡澜说,人生中最好吃的饭食,是妈妈做的。这也是胃的蛋白酶在作怪,吃了十几年,长大离家,总也忘不了那种味道。
我极爱吃饺子。而且,饺子还不能是香菇、虾仁、牛羊肉这些馅儿的,最好是韭菜鸡蛋、茴香鸡蛋或者是白菜肉的。尤其是冬天,温度低,食物不易变质,母亲便会剁出多半盆白菜,和几斤肉馅,再洒猪油搅拌。口味重的,可以伴点黑酱。平时就放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盖上高粱杆织的盖子。想吃饺子了,和面、擀皮,掀开盖子就能包上百十个饺子。春节长假回家,每天、每顿吃这个,我都不会腻烦。
另一种不会让我腻烦的是叫做马蹄烧饼的食物。我从没搞清楚做烧饼的师傅是怎样和面的,但当那沾着芝麻的一块面,在特制的锅炉里烤熟后,芝麻一面又香又脆,另一面则是绵软的白面皮。好像贝壳一样,两层之间是空荡荡的肚子,等着塞进斜刀切成片的香肠或是弹性十足的焖子。这时候,要趁热吃,薄脆和芝麻的香味与香肠或焖子的味道纠缠在一起,顺着味蕾抵达脑神经,经久难忘。
所以,对我来说,长假之旅,就是一场舌头和胃的怀旧之旅。我记性并不太好,很多年幼的事情都记不得了,很多学生时代的经历也大都忘记,但味蕾和胃肠的记忆,却很清晰。比如,高中门口马路对面有个卖包子的老太太,卖的茄子馅儿包子最好吃。后来,我又在舅舅家吃过一次茄子馅儿饺子,用比较硬的面包起来,有一种很特殊,却又难以用言语描述的美味。
这次十一长假,我回了趟高中,其间,特意跑食堂去转了一圈。挑帘子进到大厅里,各种水煮菜、劣质食用油混在一起的奇怪味道扑鼻而来。嗯,还是熟悉的、高中食堂独有的味道。久违了,一别12年,这里,还是世界上饭菜最难吃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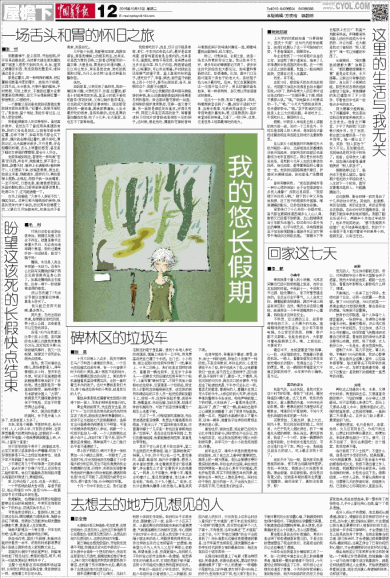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