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决定搬离我在剑桥近郊租住的房子。从卫生间的使用规则,到房租的计算法,房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申明他的英国立场,“这是你们中国人的做法,在这里根本行不通……”
作为一名研究西方史的学者,我不认为我缺乏对西方文化的敬意。但具体到这幢乡镇民居里,我与他各自分担一半的房租,因而平等地分享这个空间,凭什么你所代表的文化就要压倒我的?
事实上,房东一家也是中国人。夫妻两口儿加上两个孩子,一个刚满两岁,另一个已在母腹中待命。但他们并不天然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语言交流方式高度分裂,夫妻之间说汉英夹杂的汉语,跟孩子用英汉夹杂的英语。频繁的语言转换对他们的思维和精神究竟造成怎样的伤害我无从考究,但确乎把我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你已经猜到的,他的房东身份也像他的文化身份一样似是而非。他成为“伪房东”的过程在社会学上对一代海外“博士后”的经历具有典型意义:先是1990年代在国内读师范,然后在国内读研、读博,最后来海外读“博士后”,即 “学术打工者”,负责为导师做实验或搜集数据。然而,正是这样的被剥削者,也可以“二房东”的身份把自己租住的房间转租他人。
2
后来,我遇到了一位杨姓的广东籍老华侨有房子出租——位于米勒路的那栋二层住宅,去时,他已在门前等候多时,一个人背倚着树抽烟,树正是《再别康桥》里临水自照的金柳。
我很抱歉让他久等了,他却淡淡地说:“我不会说英语,在这里又没有朋友。”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当邻人的交谈,电视上的节目,一切作为人类社会特质的媒介交流,都与他无缘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他从人的世界里被扔了出来,扔回了动物界或生物界。剑桥,这个全球学术朝圣的圣地,对于他不过就是随便一处走向生命终点的驿站,那些令我魂牵梦绕的哥特式建筑,对于他或许只是徒然增加了空间的怪诞感。
“那您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呢?”专业旨趣使我不放过任何一个进入历史的机会。老人告诉我,在他50岁那年,鳏居的叔叔临死前通知他来这里继承家产,即眼前的这栋连排的二层小楼。这栋小楼和我正在住的那栋一样,是剑桥和整个英国城镇的特征:一面临街,另一面是或大或小的一个后花园。印象中唐宁街10号也是这种格局。
他当然是踌躇复踟蹰。把他从潮州老家的人伦秩序和意义世界中连根拔起,强迫他在新的文化生态里重新生成意义的根系,等于把一株老树提前报销了。
他就这样被交付给了眼前的这栋房子。英国之于他,其实就是这栋房子和门前这棵忧郁的金柳树。房子给予他居留英国的身份和资格;金柳陪他在树下凝望西天的云彩兀自神伤,那些云彩是徐志摩当年不肯带走的云彩。
但是,建立在一张绿卡和一栋房子上的生活如何可能?这栋房子的面积比当地英国人的民居要小许多。客厅、厨房、厕所都集中在一楼,不大的客厅里到处挂着他一家的照片,清一色的黑白照片,说明他来英国之后就不再有记录生活的兴趣了。或许,现实人生风雨飘摇,那些照片才是他安顿灵魂和托付感情的真正寓所。楼上三个小房间“品”字形地紧挨在一起。他和老伴住阴面的那一间,朝向较好的两间用来出租。按每间260英镑计算,每月500多英镑的房租就是老两口全部的生活来源了。
我来这里访学,从国家基金委按月领取的生活费是700英镑,扣除300英镑的房租,剩下400英镑,仅够一个人维持正常开销。
我如此轻率地进入他的生活,又如此轻率地退出,除了把他的个人史当做知识加以榨取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一口气跑到康河拐弯处的格兰切斯特苹果园,在这片我经常与罗素和拜伦进行想象性对话的草地,我把自诘投向这片诗与思的草地:我是不是太过矫情?国内有那么多人的生活比他差得多,你又何必到这里表现你高贵的同情?
3
李先生是剑桥华人联合会的会长,每年圣诞节的平安夜都要在他位于摄政路上著名的“万里云”饭店设宴招待剑桥的全体中国学者。我是那种从来都不敢视富贵如粪土的人,想象在装饰豪华的办公室里与剑桥的华人领袖高谈阔论,激扬文字,想不膨胀都难。当我再次来到“万里云”时,李先生正肩膀上搭着毛巾,一路碎步地在饭厅间穿梭跑堂,其时已是晚上8点。
“是不是有些意外?”
“老实说,有点。没想到您这种身份的人还亲自跑堂。”
“我回广东番禺,老家的领导要我投资。我跟他们说,我没那么多钱。他们不信,说,您看那些在香港或菲律宾、马来亚混的,哪个不是万贯家财?英国总比香港来钱吧!”
“您是怎么解释的?”
“我跟他们说,英国不比香港。英国作为一个福利国家,它的税收制度根本不可能让一个从事中餐业的人赚大钱。请别误会我的话,这里没有种族歧视,我真正要说的是,在英国这种充分竞争的社会,仅仅靠所谓吃苦耐劳或早出晚归,是不可能暴富的,事实上超时经营也是同业行会不允许的。当然,只要肯干,你也不太可能穷到吃不上饭,工会不允许。”
充分竞争的社会几乎穷尽了暴富的可能性,或者说将这种可能性仅仅限定在乔布斯这样永远的创新者身上。
毕会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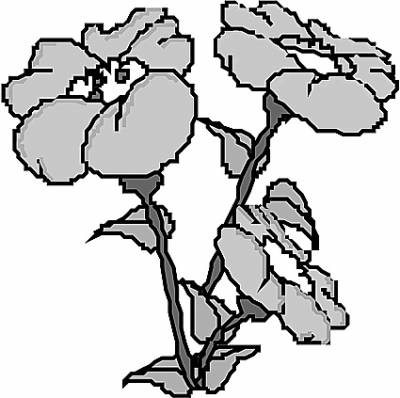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