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2013年或会成为中国“反腐元年”。我的朋友、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对此充满期待,并于近期发表《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本版2012年12月31日刊发),认为“如果人心不正、风气败坏,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时难于登天”。我的另一位朋友、南京晓庄学院邵建教授,则发表《正人心以正制度,还是正制度以正人心》一文批评方教授的观点,认为“道德之善依赖于制度之良”,主张从“正制度”入手反腐,否则“道德的调子越来越高,正如腐败本身会愈演愈烈”。
两位教授关于“正人心”与“正制度”的争论,恰是几十年来围绕反腐问题提出的一系列针锋相对观点的集中体现,如人性善/人性恶、人治/法治、德治/法治、传统/现代、道德反腐/制度反腐、中国经验/西方经验,等等。不过,“正人心”和“正制度”两者看似截然相反,实则互相含摄,同为反腐大计,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还是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思是,政治成效与道德君子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有道德君子则政通人和,反之则政乱人殃。关于这一点,荀子说得更加明白:“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
孔子和荀子的话,的确体现出儒家具有的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但并不能由此就推导出儒家是单向度的“道德决定论者”,相反,儒家非常重视制度建设,且对中国政治贡献良多。史家陈寅恪就认为:一部《周官》(即《周礼》)集先秦官吏制度和政治制度大成,历经秦汉,及至魏晋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
儒家在推动人心和制度共建时,特别强调三点:一是两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故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二是“正人心”以发挥预防功能,“正制度”以发挥惩罚功能,故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三是《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当然,“正人心”首先是一种对政治精英的道德自律要求,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故儒家向有“正君心”和“格君非”的传统。
中国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与其说暴露了儒家治理模式的一些弊端,就像批评者所说——即使朱元璋对贪官实行剥皮的酷刑严律,亦未能杜绝官吏腐败和避免王朝覆灭,毋宁说是这些王朝并没有很好地践行儒家的主张,没有充分发挥“正人心”与“正制度”共建,在推动社会健康运转和政治良性发展方面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以史观之,中国历代王朝开国之后,一般先是经历短时期的“马上打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乎”之惑,不久就会回归“拨乱反正、复古更化”的传统之路,恰恰说明了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强大生命力。
事实上,现代西方在社会治理方面固然非常重视制度建设,但同样强调“正人心”的作用,认为在道德的荒漠上,不可能坚实地建立起任何伟大的制度。不明乎此,就不会明白“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为何在完成《国富论》之后,又推出一部《道德情操论》,更不会明白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为何曾说:“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即此,我们可以说,既“正人心”又“正制度”,本是中西双方共有的一大传统。
遗憾的是,中国现代社会肇造以来,既将中国“正人心”和“正制度”有机结合、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全盘打倒,又在学习西方制度时忽略了其重视“正人心”的一面。延宕至今,我们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反腐问题,相反却陷入了“坏人心”和“恶制度”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陷入了“深度腐败”亦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人人向往甚至努力践行的困境,陷入了“人心甚不美”和“制度甚无力”的泥沼。
腐败是政治的杀手,更是社会的毒瘤。走出“道德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无谓争论,既加强“正人心”建设,重拾礼义廉耻,重建国之四维,又加强“正制度”建设, 尊重本国传统,学习西方经验,臻于仁政善治之美。
相关文章:
慕朵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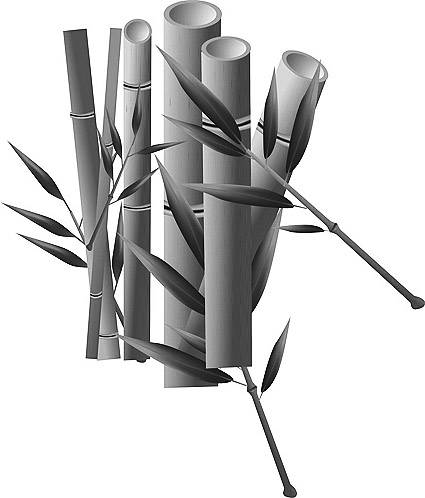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