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无大事,尊严往往就隐藏在小事里。隐藏在小事里的大事,便是精神出路太狭窄导致的尊严扭曲。
赵凤,44岁,女,翁古城张炉乡翁南村小王屯小队,2009年7月喝百草枯自杀。姜立修,43岁,男,翁古城石岭乡槐树沟村下黄小队,2008年6月喝百草枯自杀。曹运宽,63岁,男,翁古城曹崴子乡四家子村柳店小队,2009年5月上吊自杀。如果将这个名单继续列下去,将会有长长的一串。从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5年时间,某地区自杀死亡名册上,有500多例。这是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中偏低的数字。据了解,在中国,80%以上的自杀死亡发生在农村。这些数字不出于某个档案,它们被记录在一部非虚构作品《生死十日谈》中。近日,该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
作者孙惠芬以“在场”的方式,记录中国辽南农村自杀问题,通过寻访自杀遗族的声音,分析当下农民的精神生活现状和情感困境。当然,为了保护家乡,孙惠芬将事件具体发生的地点隐去了。
“揭伤疤”项目是一种治疗
以前,农民的自杀很少闯入孙惠芬的视线,即使有,她也很少了解其具体姓名。改变发生在2011年。
这一年的秋天,孙惠芬在乡村采风半年之后,大连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为做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带领课题组深入到她与孙惠芬共同的故乡。早在2007年,孙惠芬就与贾树华相识。“当时我有过写一部虚构作品的念头,但因为对故事发生的背景有隔膜,就没有动笔。”错过一次的孙惠芬在2011年“终于跨出去了”。
这一年,孙惠芬与课题组再次深入农村。第一天,他们来到张炉乡张店村村委会。妇女主任拒绝带他们去采访:“你们问什么状态?家里有人死了能是什么好状态?再说,你揭人家伤疤,谁能愿意?”
确实,如要从死者亲属口中了解事情的真相,就必然要揭开伤疤。采访者如何能尽量不让被访者感到“疼痛”,又能探究事情的来龙去脉,成为课题组的一个难题。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孙惠芬只是一个倾听者和观察者。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因为怕影响这个项目的时间进程,我并没有更多的访谈机会。事实上从县到乡再到村,最后到个人,课题组做了大量工作。他们需要让人理解这个‘揭伤疤’项目,其实是对灾难家庭进行救治和干预的过程。之后在调查中,努力去对受访者受伤的心灵和心理疾病予以抚慰和治疗。”
从“揭伤疤”到帮助、治疗,课题组需要尽可能地找到更多知情者,还原事情真相。“这些自杀者的生死日期确凿,名字醒目。赵凤、姜立修、曹运宽和三岛由纪夫、杰克·伦敦、张国荣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以及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外边人很少知道。”孙惠芬在书中痛楚地写道。
尊严隐藏在小事里
“十日谈”,复原了十天的访谈现场,将多个人的命运串联在一起,有点像一部“纪录片”。
通过孙惠芬的讲述,读者会发现,在中国当代乡村,死亡的秘密只有通过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母女关系等关系链条中的种种琐事,才能找到痛苦的线索和答案。
就像书中写到的第一个案例——“一泡屎要了两个人的命”。
2007年,于家的儿媳妇去河边洗衣裳,把孩子留给婆婆照看。婆婆到园子里打芸豆架,把孩子自个儿扔在炕上。儿媳妇回家一看,孩子在屋里抹了一炕屎,便火了,骂起婆婆,还扯她衣裳。婆婆一天三顿饭地伺候儿媳妇和孩子,可儿媳妇还冲她动手,她气不过,摸出一瓶百草枯喝了。喝完,怕儿媳妇喝,把家里的农药都倒了。儿媳妇看婆婆倒在院子里,到底还是在灶屋后的窗台上找到一瓶卤水,结束了生命。或许对生与死的判断不似常人所想。在某些人眼里,“死,不是失败,而是胜利。”这是孙惠芬对这一悲剧最简练的描述——婆婆不想让媳妇死,就是为让她感受生的痛苦。
由类似案例,孙惠芬发现,“在旁观者眼里的小事,正是当事者跳不过的大事”。她认为:“生活无大事,尊严往往就隐藏在小事里边。而隐藏在小事里边的大事,则是精神出路太狭窄导致的尊严扭曲。”
在孙惠芬看来,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痛苦都是平等的——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痛苦就比农民的痛苦更有分量。“在人类精神面前,没有高下、贵贱之分。只有麻木和敏感之分”。在她看来,这是作家的职责:应该在探索人物心灵历史的同时,揭示人类本身的存在处境。
精神缺乏宽阔出口
“每个时代的自杀都与当时的环境有关。在我有限的了解和有限的案例背后,我觉得,主要还是由于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精神出路太狭窄,乡村医疗、心理干预欠缺、科学教育落后造成的。当前,中国的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经受了种种震荡,物质的富足和精神的匮乏,无法使他们在精神上拥有强有力的支撑、宽阔的出口。”她这样分析道。
“每一个时代都有悲剧,这些悲剧折射着人的存在境遇。我不喜欢悲剧,却写了这样一部书,是因为从那些悲剧中看到农民的尊严和高贵的情感,看到他们在黑暗里向着光明的挣扎,看到他们的坚韧和坚强以及自我救赎的力量。”
如何更有效地解决这一现状,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个观察者和书写者,孙惠芬发现:“专家们的问卷访谈,其实是对受访者的真正抚慰和心理治疗,那些密封着伤口的忍受煎熬的受难者,其实最是渴望心灵之窗被捅破、被打开、被理解的。”
除了帮助受访者治愈心灵创伤,以有效方式减少自杀现状也十分紧迫,对中国乡村群体的精神关照,尤为重要。“事实上,无论贫穷与富裕,精神从来就没从世界退场,也不可能退场。”她强调,“在时代的急速发展中,或者某一个时刻应该慢下脚步,往灵魂深处看一看,了解人们内心的真正需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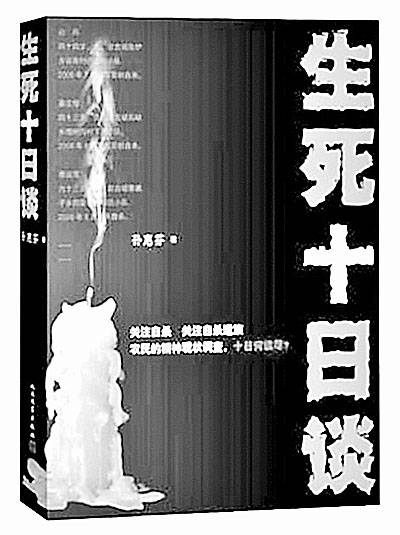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