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我非常嫌弃一张脸:脸挺大,眉毛很长,鼻梁不够高,下巴不够挺,嘴唇有点薄,关键是……“那嘴歪歪的!”母亲说完,哈哈笑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嘴唇上有块疤,结果那嘴就歪了。”
每当有人偶尔夸我长得好看时,母亲便会有这种反应:“好看什么啊!”然后,就会说起我这个谜一般的嘴唇——问遍家人亲友,谁都不知道我上嘴唇的疤痕是从何而来,然而,它从此成了我挥之不去的阴影。
作为一个不爱照镜子的人(大概潜意识里也不想心塞),我看到自己这张脸的机会很少,所以对它所有的评判都来自外界,尤其是母亲。而母亲又经年累月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缺点所在,很早就让我认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我很丑。
自打小学开始,这个印象就深埋我的心底。当同学们在操场上追逐打闹,或者挥着膀子玩“摔四角”的游戏时,我则趴在教学楼的栏杆上,忧郁地望着远方和远方的远方,为自己长大后的命运担忧。我想,我这么丑,以后一定追不到姑娘,最终得打一辈子光棍。别看我小,也知道光棍是什么意思。离我家不远,就住着一个光棍,村民们见了他经常开玩笑,各种玩笑,甚至连我们这些小不点也毫无顾忌地跟着起哄。在农村里,光棍是没有尊严的。
当然,我那会儿还小,不会懂尊严为何物,却理解被嘲笑的滋味。小时候因为丑被嘲笑,长大后再因为打光棍被嘲笑,把人生活成一个大写的笑话,这该多悲哀。整日里我想着这些悲哀的事,头发也渐渐在哀愁里变白。到现在,人们还常问我,怎么那么多白头发,我只好回答“忧国忧民,操劳所致”,哪里好意思说是因为从小愁媳妇。
虽然我估计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承认,但我知道父母还是很爱我的——或者用“关心”更容易让他们接受。但是,我生活在一个不懂如何表达感情的家庭,别说公开表达感情,二老甚至低调到从来不会表扬我,当别人表扬我时,还会忙不迭地指出我的缺点,证明对方虚伪,或者是告诉对方别被我蒙蔽了,要拨开云雾看到我的本质。
记得中学有段时间,我一直给一份杂志投稿,但从来没被刊用。那会儿的编辑比现在真诚很多(我的编辑看到这里还能容忍这篇稿子发表的话,当属例外),还会给我写退稿信,不长,寥寥几句,以示鼓励。所以人家是写字换钱,我则是写字换信,相当于交了个笔友。
有天下午,我挥汗如雨趴在柜子上又给笔友写信,大伯有事来我家,和母亲闲聊时,大概是我问在干什么,母亲便说起我的退稿生涯。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母亲应该是因为家里还有个文学青年而感到自豪的,但是性格又不允许她当着别人的面夸奖我,于是哈哈声又起,她特意说起了我的退稿故事——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故事。那时候,我还不懂欲扬先抑的技巧,只当母亲在出我丑,我强忍着,等大伯走后,终于爆发,为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尊严。
如是看来,文学在我心中的地位还是要高过令我愁白了头的这张脸,我从来没有因为母亲说长得不好看而爆发过,只是默默接受这个现实。也因此,我从小学就开始早恋,有了喜欢的姑娘。祖先教育我们说,笨鸟先飞,那丑人就要早恋。
当然,大部分时候,我都是暗恋,倒不是担心表白被拒绝,而是害怕对方难过:你这么丑,也敢喜欢我,是觉得我可能配得上你吗?!
我已经很自卑了,就不要再伤害别人。
高中时,有次和一个暗恋的姑娘吃饭,她忽然看着我说:“你的眼睛真好看啊,你妹妹一定也很漂亮吧。”天啦噜!我长这么大,除了家里一个老太太说过我的眉毛和周恩来一样,这是第一次有人夸我长得漂亮——虽然是局部的——而且还是我暗恋的姑娘。我当时心底被压抑了十八年三个月零五天的外貌自信、恋爱自信、结婚自信都被激发出来了,当即就打算向她表白,如果她同意,我以后就非她不娶了。
我心里越是盘算,越觉得未来可期,一个光明的、幸福的人生开始像我招手。我抬起头,红着脸,怯懦着那张歪歪的嘴,正打算对她说话,她抢先半秒钟开了口:“我挺喜欢你们班王龙的,他有女朋友吗?你能帮我把这封信交给他吗?”
到现在,我都很纠结一个问题,当初她那么夸我,到底是真心的,还只是为了讨好我,好为她撮合与那个男生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我是继续生活在丑陋的阴影里,还是重新认识自己,开始另一种人生。
张恒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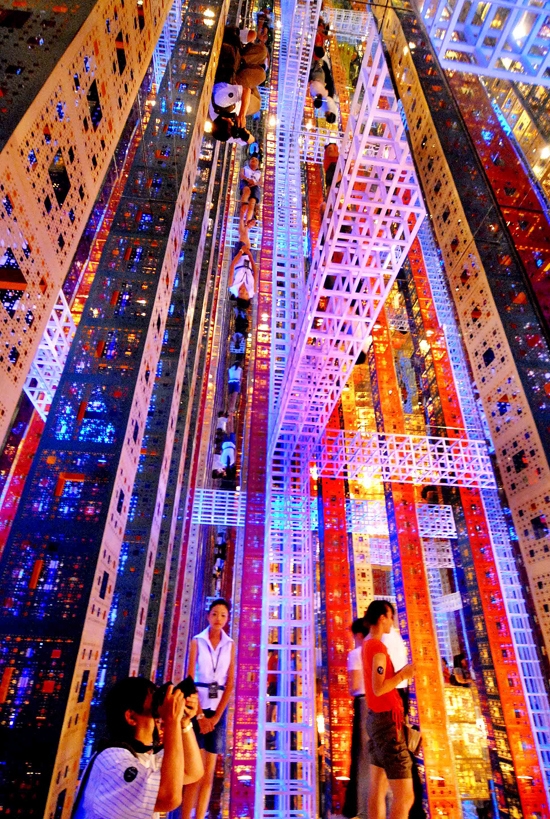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