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孩子具备生存能力,学习能力却很弱。我知道他们应该待在普通学校里,但是学校能给他们多少?我真的不知道”
□“其实,整个学校对于我们,就是一个大资源教室。却很少有人想过来问问我们,该怎么建?”
□“我希望特殊儿童的家长不再唯唯诺诺地说‘我的孩子给你们带来了麻烦’,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勇敢地说出来:当我和这个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
-----------------------------------------------------------------
陈小赫觉得,自己在教室里的存在,就像是一个未经安检的“易燃易爆物品”。
“我被老师安排在了角落的位置,这样和同学的身体接触最少。”小学五年级放学之前的一个下午,班主任老师大声提醒全班同学:“同学们下课了尽量不要去和陈小赫玩,他眼睛看不见,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时,陈小赫正在拿着笔奋力读完最后一段课文,他说自己“一下子听得眼珠都要掉了”。
距离北京1000多公里的浙江嘉兴,一所普通初中,班上“相依为命”的“超哥”和“楠姐”却因为班主任把自己安排到了后排感受到了全身心的愉快。“他们一分到我们班,我就蒙了。经常上着课他俩就从座位上腾地站起来,随意走动。我只能让同学们忽略他们的存在。”在班主任孙老师的认知范畴之内,自己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等他们不在的时候,告诉全班同学不准欺负他们。他们是智力障碍,受法律保护的”。
在教育学的概念中,陈小赫、“超哥”、“楠姐”都属于身体有残疾的“特殊儿童”,他们在普通中小学里接受义务教育叫“随班就读”。尽管接受义务教育是所有孩子的权利,但特殊儿童的随班就读之路走得异常艰难。
从“特殊照顾”到“资源教室”
最近,一篇题为《教育,是温柔对待每一个想要成功的孩子》的文章在网络上以及微信朋友圈里被大量转载,作者纪寻是一名神经肌肉病患者,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巴黎政治学院。文章记述了她在南京读中小学时的种种不易:被分在四楼的班级,没有人会想着把楼上楼下的班级换个位置;厕所在一楼而且没有马桶,她只能“站着”上厕所,招来围观和指责,但没有人想过应该为残障学生修一间无障碍厕所。
不过,特殊儿童的随班就读之路以后有望更为顺畅,因为,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普通学校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中指出“招收5人以上数量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一般应设立不少于60平方米资源教室以提供特殊教育专业服务”。
《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普通小学、初中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招收的学生3.80万人,在校生20.91万人,分别占特殊教育招生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53.78%和52.94%。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中心王雁教授介绍:“资源教室在普通学校中的推广和普及,其实正是中国融合教育支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从认知到行为,‘资源教室’其实都涵盖了。”
当然,这个指南要落到实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学生总在入学升学,一间资源教室怎么满足得了不同残疾类型的学生?”于老师是一名“战斗经历”丰富的“随班就读”老师,收到“指南”消息的当天,心里的疑问也出来了。
“我们不过是不对这些残疾孩子做普通学生要求罢了,至于全方位介入他们的学习,那是个多大的工程?目前我们还没有条件弄。”这是一个硬件设施一流的省一级重点中学教导主任的第一反应。
对于这群特殊的孩子,到底是怎样的观念在主导教育?
“只要安全,就是一切”?
随班就读到了四年级,陈小赫的视力衰退到了极限。妈妈王楠第一时间被班主任老师叫去签了一纸“军令状”,上面写着“孩子若继续在学校内学习,出现任何意外事故,学校概不负责”。
“孩子出事儿,我自己来兜着!”这是王楠的口头禅,也是陈小赫一年年得以顺利升级的通行证。
教室东南角的课桌,是属于陈小赫的。那里常年放着一个小型的电子放大器、一副望远镜,靠墙是一根盲杖。陈小赫说:“这些都不是电子设备,老师让带。”
其实,陈小赫最想带去学校的,恰恰就是他最依赖的一件电子设备——那个装着读屏软件的电脑,这个阅读和写字相当吃力的少年已经习惯了用电脑键盘和外界交流。然而,“哪里有插电源的地方?”“键盘的敲打声会不会影响别的孩子学习?”“电脑弄坏了谁负责?”老师的一串反问,让陈小赫选择了沉默。
沉默,可能是老师们在面对这群“风格各异”的特殊孩子时,最希望看到的。一次,“超哥”用拖把堵住了学校公共卫生间的马桶。孙老师爆发了:“你这个奇葩!你像隔壁班莉莉一样不说话、不乱走,每天上课就睡觉,不就好了?”莉莉是“超哥”和“楠姐”的玩伴,他们因为每次升旗都落在最后而互相认识。在以“超哥”为首的帮派里,集结了一个年级中6个这样的学生,他们自发一起吃饭、上体育课。
同样安静不下来的,还有卢杰,一个患有情感障碍伴随轻度智力障碍的11岁小学生。“捂住他的嘴巴,从肩膀处把他用力按到座位上。这个工作,每节课的频率起码是8次。卢杰到了课堂以后,我的工作时间几乎成了原来的两倍。”班主任高老师无奈地说。
高老师和校长沟通,得到的答案是:“义务教育,只要是家长送来的孩子,我们都要收下。”
高老师一直坚持这个观点:“真的爱孩子,会把这样的孩子送到特殊学校里。”
把孩子送到特殊学校里?陈小赫的妈妈3年前有过这样的想法,“看到里面一个个中度残疾的孩子,最终还是不忍心。孩子本来好好的,为什么要让他走进那个狭小的世界学用处有限的盲文呢?”
“老师对他没有任何的要求。只要不出事儿,就是尽责。”王楠这位原本在外企叱咤风云的职场女性,已经做了5年的“全职妈妈”。从四年级到初中,陈小赫只去学校半天。另外半天,陈小赫在家中弹钢琴、阅读、学外语。“甚至是生理课,也是我红着脸在给他讲。”王楠说。
幸运的少数
“随着椅子倾斜的角度,往后靠,头上仰,释放坏情绪;往前倾,他们的腹部顶住大腿,寻找本体感,这就是摆位椅。”北京东城区西总布小学教学主任孙全红老师说,这样的椅子,几乎给每一个就读的自闭症孩子准备了一把。
这个早在2001年就建成资源教室的小学,现在接收了8个残障儿童:自闭症、言语障碍、智障、听障、情绪障碍、肢残,孙老师说得出每个孩子的症状和作息时间。
北京市特殊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孙颖介绍,北京市从1998年开始筹备建设资源教室,截至2015年10月,全市有资源教室的学校是290所,兼专职资源教师565人。
休息室里,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正在熟睡。下午的课对他来说,有时难以坚持。年轻的助教老师看护在身旁。
这样的“助教老师”,在这所学校里一共有3名。这是种一对一的支持和陪伴,“她们和孩子并排坐着,对孩子,就是一个标杆。”孙老师说。
杨老师做马天天的助教已经5年了。这个高大、长睫毛的小男孩患有自闭症和智力障碍。在助教老师的带领下,他能起立、问候、书写、朗读,把作业本一一放进贴有“语文”“数学”“科学”的资料袋里。
“像在挤剩的不多的牙膏,但是还得挤!”杨老师这样形容辅导孩子在学校追赶同龄人脚步的场景。
“天天还算是幸运的。只是,这样的学校,在全国到底能有几所呢?其他孩子又是怎么过的?”杨老师总担心,天天升到别的学校后会如何。
在这所学校里,残疾孩子被提出了同等的学习要求,“让他们先去做,不行,再来做补充。”四间用途各异的“资源教室”每天都有孩子来做过训练的记录:“思维训练、动作训练、学科补救”,这些课程被排成了这个学校里第二张“总课表”,被孙老师拿在手里。
“建设完备资源教室、接纳更多残疾孩子就读,这根本不是一个可以分清第一步、第二步的事情。这些孩子的需求,只有在不断进入普通课堂时才能被发现。”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执行理事会成员蔡聪说。
“如果学校能成为一个大资源教室!”
初一开学第一天,陈小赫又兴冲冲地跑进了女厕所。听到了女生们惊慌的呵斥声,陈小赫赶紧撤退:“学校卫生间标志牌上的字为什么不能再大几倍呢?和主任说说去!”
“和主任说说去。”这几乎成为陈小赫在四年级以后悟出的“生存哲学”,因为很多事情,和班主任老师提了“她不敢答应”。那年,他10岁,经历了6次手术之后,右眼彻底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01,存有部分光感。“能看清楚的字,从小四一下变成了三号。看书速度,是别人的三分之一。不过学校里哪儿有给我看的大字课本呢?”陈小赫反问。
与心智健全的陈小赫不同,“超哥”和“楠姐”特别希望“和其他同学一样”。每次考试,即使不会被老师算入总成绩,他们都要把试卷收集得一张不落。成绩一出,“超哥”便拉着“楠姐”去问成绩:“老师,这次我们考得怎样?”
“这些孩子具备生存能力,学习能力却很弱。我知道他们应该待在普通学校里,但是学校能给他们多少?我真的不知道。”孙老师不止一次在班主任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
面对需求多样的“特殊学生”,教师到底可以做些什么?王雁教授主持的一项针对“随班就读”教师专业素养的研究,将“教师获取外界支持的能力”也作为衡量因素。“老师应该作为能动的个体,主动向外拓展资源,寻求对这些孩子的应对方案。因为我们对于残障孩子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支持体系本身还是不完善的。”王雁教授说。
看着陈小赫磕磕绊绊长大的这5年里,王楠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根“紧绷着的弦”。陈小赫一遭遇不公,她必须保证自己第一时间出现。“陈小赫,你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这是母子俩见面打招呼的方式。
对于同学们的态度,陈小赫只是淡淡说了句:“有时候,他们会不理解不耐烦,他们长大了,就都明白了。”15岁的陈小赫,好像是“已经长大了”。在陈小赫的学校里,有近10个不同程度智障的孩子,陈小赫常常跑去他们的教室问问他们喜欢些什么。
在两幢教学楼之间,是一条陈小赫每日必经的外挂式楼梯,没有任何提醒标志,凶险万分。人来人往,陈小赫把脚步放得很缓很缓。“其实,整个学校对于我们,就是一个大资源教室。却很少有人想过来问问我们,该怎么建?”陈小赫望着这所每学期都被翻新、添置新设备的学校,就这样被一次次与己无关的陌生,推向谷底。
在《教育,是温柔对待每一个想要成功的孩子》一文中,纪寻最后这样写道:“我希望特殊儿童的家长不再唯唯诺诺地说‘我的孩子给你们带来了麻烦’,希望学校不再以健康状况为名向他们关上教育的大门,希望教育工作者们不再对他们的需求无动于衷,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勇敢地说出来:当我和这个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
(文中提及的特殊儿童及家长均为化名)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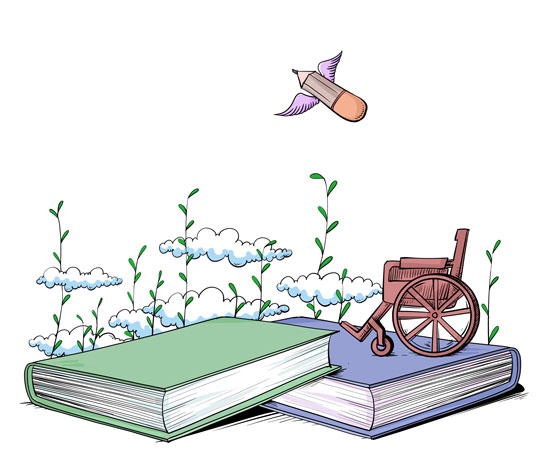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