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岁时,母亲所在的元件十五厂倒闭。母亲像个插班生一样,到了元件七厂。这两家都是加工电视机零件的。
暑假里,爷爷奶奶没空照料我,我就随母亲去她厂里待着。母亲在前头骑车,总也不记得回头望望跟在后头的我,我提着心,害怕跟丢了母亲。
小城在长江尾,无数的支流汇入长江,母亲的厂子就在一条小河旁。河水浑黄,水面宽阔,有船家经过就会响起“呜——呜——”的鸣笛。我骑着一辆亮粉色的小自行车,在那条狭小的泥路上,蹬得飞快,车把手快要剐到一侧的房子。
进了厂子,扑鼻而来的是一股子油漆味,偌大的、水泥浇筑的厂房,一排排亮晃晃的白炽灯,数条流水线依次排开。那些叔叔阿姨坐在流水线旁,我从小怕生人,跟在母亲身后,在叮嘱中把那些叔叔阿姨一个个问候过来,他们转过身和我打招呼。
母亲也同他们一样,穿着灰色工作服,坐在流水线的一端。我坐在她身旁的一个矮凳上,从下往上看母亲。
母亲的头顶有一盏小亮灯。在一圈光亮中,母亲伸着脖子,手持一个小镊子挑拣次品。流水线上走的元件,是我到初中物理课才懂的,其实就是一段电阻,一圈红色、一圈棕色、一圈黑色,代表不同的阻值,我都当着好玩把一个一个串起来,当戒指、当项链。
厂子里两班制,早七晚七。午休时间,母亲总在补觉,在屋子里我都是踮着脚尖,生怕惊醒睡梦中的她,引起一番恼怒。尽管现在,我也避过中午时段给她打电话,20年来这是她固定的休息时间。
母亲的日子并不好过。机械的工作节奏、压抑的环境、被老员工欺负、替人顶包,母亲年轻气盛,不会圆融之术,往往自己被气哭。我总爱坐在墙头等母亲回来,远远看到她,便奔过去跳上她的车,唧唧歪歪地说个不停。可母亲太累了,到了家,就独自躲到楼上去休息了。
我上六年级,母亲准备换工作。那时高清电视开始普及,元件七厂面临技术淘汰,同样被淘汰的还有工人。母亲高中毕业,经人介绍在一家快餐店当服务员。
那时,我开始进入叛逆期,觉得母亲的工作不值一提。我也已经长大到暑假不需要跟着爸妈去上班了。那家店在城市的市中心,和朋友玩总是绕不开闹市区,但我也很少走进那里,尽管有人提议,我也想方设法绕开母亲工作的地方。
有一次,我去她的店拿东西。我坐在餐厅一角,母亲给我端来一大袋子薯条——超过标准量的薯条。我把一根一根薯条塞进嘴里,一边四处张望着。
人流里的母亲很显眼,鲜艳的T恤、深蓝色裤子,戴一顶有餐厅标志的帽子。她个子不高,嗓门尖锐,在人来人往的餐厅走得飞快,忙着收拾托盘、擦地,累了就撑在拖把柄上偷点小懒。碰到熟人就开心、热情地打招呼,但也不敢聊天太久,偷偷说“怕经理见到不好” 。
其实,就算是经理,他年纪还差着我妈一大截,餐厅员工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活泼。母亲性格热情、内心阳光,和年轻人凑在一起,经常嘻嘻哈哈,大笑不止,魔音穿耳。
后来,我离开小城去念书、工作。一天,收到她微信请求要求加好友,“我是妈妈”,这才知道她买了智能手机,同事还教会她玩微信。有时一个上午她“嘟嘟”发来十几条,我常回复一条“在写稿”“在工作”“在采访”,转眼收到她一条,“工作!工作!都是借口!”
今年,母亲52岁,过了退休年纪,还是决定要接着干,不愿过清闲生活。我还记得,当我坚持留在外地工作时,母亲昂着头,骄傲又挑衅地说:“我赚的可不比你少!”
曹忆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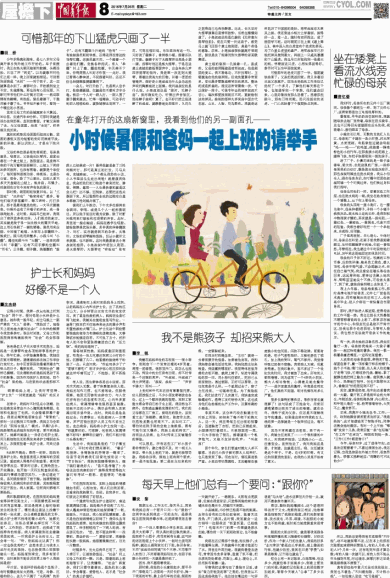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