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每年都会定时、定点发生的“战争”,时间通常是夏季与秋季,战场覆盖中国从北到南的产粮大省。
丰收时节即是兵临城下的时刻。大战一触即发。政务公文里不断出现“攻坚战”“迎头仗”“硬战”的字眼。战况之艰巨,从作战手段可见一斑:卫星遥感监测,载人飞机、无人机“空中围剿”,地空一体巡查, 24小时轮班“严防死守”。
作战标语更是遍地开花:“飞机已经上天,地里不准冒烟”,“上午烧秸秆,下午进班房”,“人生道路长漫漫,焚烧麦茬找难看”……
敌人不是什么外来入侵生物,而是那些散落田间、枯槁发黄的秸秆。它们为人类捧出了粮食,转身就成了麻烦制造者。
现在,又一个战斗的季节来了。
阻击战
在各大“粮仓”,秸秆禁烧的阻击战投入不菲。据公开报道,仅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一个区的25个乡镇(街道),去年为秸秆禁烧投入的财政资金就达4458万元。而在湖北省荆州市,今年夏收期间,每天1323个督查组、35280个巡查组,24小时轮班在地头巡查。
“顶风作案”者一旦被发现,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工作不力的地方官员为此被摘掉官帽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农民而言,烧,几乎是处理秸秆的首选方式。只要一把火,不花钱不费力。祖祖辈辈留下的经验让农民相信,秸秆焚烧后留在田里的草木灰,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虽然也有研究表明,土地中的微生物被大火“烤死”之后,耕地的生物环境反而会被破坏。
真正让秸秆焚烧成为重点阻击目标的,是最近几年各地大气污染“雾霾围城”的困境。秸秆焚烧产生的颗粒物PM2.5虽然不到PM2.5总量的5%,但由于秸秆焚烧通常都在短时间内集中焚烧,因而在这期间,最严重的时候,烧秸秆大概可以产生空气中PM2.5的三到四成。
中国农作物秸秆总量几乎占据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组织各省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的评估显示,2015年全国主要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为10.4亿吨,可收集资源量为9.0亿吨,利用量为7.2亿吨,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0.1%。
所谓利用,包括使秸秆能源化、肥料化、基料化、饲料化和工业原料化。各地都在劝告农民“秸秆还田”能增产,理论上一点也没错;实际上,有时候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潘根兴是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他下乡考察时,常有农民反映,在一年两季、农时很紧的情况下,大量的秸秆铺在田中,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腐烂成养料。新的作物播种后,许多苗长在了秸秆上。农民形象地把这种“脚离了地的苗”叫做“吊死苗”,自然是长不好。
更糟糕的是,“秸秆还田”有时还好心办坏事。
人们希望秸秆还田能够给新苗提供更多天然的养分,但秸秆分解得靠微生物来“作业”,微生物又需要吸收足够的氮才有力气来消化秸秆,结果反而是秸秆在和新苗争养分。
如果上一茬作物的病虫害留在了秸秆上、传给了新作物,情况就更不妙。这种情况下,秸秆还田了,农民却不得不多施化肥、多打农药。
因此,每年夏收秋收季节,神州大地,处处冒烟,很多农民喜欢一烧了之。
为何秸秆禁烧这场仗就是无法彻底打赢?战争面临的一个形势是,如今的农村,秸秆多,人力少。
江苏农民王文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他所在的江苏淮安市凌桥乡,两万人,6万亩地,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前几年,凌桥乡的农民偷偷摸摸地烧秸秆是常有的事,“农民也是没有办法”。
2014年,王文石跟人合伙开了一家“联创利用合作社”,专门跟秸秆打交道。他们买了20多台大型机械,免费为农民收集秸秆,农民也不向王文石收费,“双方互免”。收到秸秆后,再卖给秸秆利用的企业,以此挣钱。
两年下来,王文石的企业已经成为江苏规模最大的从事秸秆收集业务的企业,业务还做到了安徽和湖南。
然而,面对燎原之势,他所做的只是杯水车薪。
条条大路不通罗马
如果秸秆还田这条路子行不通,其他的“作战”路线倒是还有几条。只是,在潘根兴看来,它们都各有各的缺陷。
秸秆可以用来造纸。“但纸用完以后,还是废弃物。而秸秆制成了纸,其中含有的氮和磷没能得到利用,反而加大了废水处理的难度,比芦苇造纸的环境成本高。”潘根兴点中了一个“死穴”。
秸秆还可以给牲口当饲料。但如今的农村早已不是田园牧歌的景象,大规模的养殖场大多建在城市周边。未加工的秸秆质量轻、体积大。一辆可以装1吨水的车,装煤可以装1.3~1.5吨,但装秸秆只能装200~300斤,等于1吨秸秆需要分5车运。运输成本决定了这不是划算的买卖。
运输成本同样影响了把秸秆送去电厂这一条“直燃发电”的路。潘根兴看到,不少生物质发电厂现在反而转向了烧煤。“秸秆回收成本高,运输费用高,燃烧后的废灰又难以处理。相较起来,还是能够机械化生产的煤比较划算”。
在潘根兴眼里,“看起来比较理想的办法”,是用秸秆制沼气。但是,在东北等寒冷地区,沼气只能在气温高的季节才能生产,而在江浙一带相对湿热又相对富裕的地方,“谁会愿意每天围着一个沼气池转,每天把里面的东西掏进掏出呢?”
更为重要的是,在潘根兴眼里,以上每一种方法都无法避免一个问题——浪费。秸秆中含有养分、能量和纤维,以上的每一种方法,都只能利用到秸秆的一种特性。
“人人有办法,处处皆烦恼”,潘根兴在一篇论文中这样形容目前的秸秆利用现状。简直是,条条大路却通不到罗马。
如何才能为禁烧战觅得一套“几全其美”的战术?周世丰供职的这家外企手中,算是握有一个“锦囊”。
丹麦诺维信公司是全球工业酶制剂和微生物制剂领域的主要生产商之一。周世丰是诺维信在中国的生物炼化业务的总监。他在电脑上向记者演示了一幅秸秆切面的示意图:最外侧是红色的线条,这代表秸秆外层的“木质纤维素”。红色线条中间交错着的是蓝色和绿色的线条。蓝色线条的是“纤维素”。剩下的绿色线条,状如打结的毛线,这就是“半纤维素”。
将酸或碱加入秸秆之中,红色、蓝色、绿色的线条,在化学、物理综合作用下,统统被“剪碎”。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下一步进行得更顺利:将酶加入进去进行催化。在酶的作用下,蓝色、绿色线条中的大分子被切成小分子,最终转化成糖。糖再经过发酵、蒸馏,就变成了乙醇。而发酵后的固形物残渣也不浪费,可以作为燃料来直燃发电。
更厉害的是,如果将秸秆制成的燃料乙醇,按照10%的比例加入到汽油中,调和成乙醇汽油,与普通汽油相比,可使汽车尾气中的碳氢化合物浓度下降42.7%,一氧化碳浓度下降34.8%,这两项有害物质恰恰是PM2.5的主要组成物。
潘根兴手里也握着一个“国产”的“锦囊”。
他这个法子好比:“将一块肉骨头,放入锅中,盖上盖子,慢火细煨。再打开后,锅中不仅有炖烂的肉,还有汤和扑鼻的香气。”
秸秆就是这块肉骨头。在密闭系统中,通过数百摄氏度高温加热,秸秆中的生物质发生热解作用。分离得到固体的生物质炭(肉),液体的木醋液和提取液(汤)以及气态的生物质气(香味)。
这些分离得到的物质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生物质炭可用于农田施肥和环境污染处理。在整个过程中,秸秆的所有物质,没有废弃或浪费,产生的热能也可以用来发电或供热。
用这种技术,每处理一吨秸秆,就可以减少0.7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规模产业化后,这些减排量,还可以拿到碳交易市场上去交易。
无利可图中的出路
技术上的“锦囊妙计”虽好,可是如何才能用于“实战”呢?
在国际上,丹麦是公认的秸秆利用最成功的国家。丹麦驻华使馆能源参赞熊强(Thomas Shapiro-Bengtsen)介绍了这个北欧小国的制胜秘诀:“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有经济利益上的激励……比如,在丹麦,如果你选择用生物质替代化石燃料,那么会有不同的税收优惠。”
丹麦的萨姆索岛是丹麦“绿色童话”的极致体现。这个岛,在能源学家索伦·荷满森(Soren Hermansen)的带领下,实现了100%能源永续利用。其中,全岛的供热主要由两个秸秆供热厂提供。
在发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邮件中,索伦·荷满森解释,要说服岛上居民们加入秸秆利用的行列中来并不难。“因为用焚烧秸秆供热比用油便宜。而且供热厂也是由当地居民共同所有的合作社性质。用户实际上也是供热厂的拥有者。”
从丹麦的经验来看,要打赢秸秆禁烧这场战,还得“利字当头”。而眼下,在中国,秸秆利用产业“无利可图”,也正是卡住整个产业链齿轮的那粒石子。
对许多农民来说,收秸秆,就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负担。在江苏,算上政府补贴(苏北25元/亩,苏南35元/亩),农民每收一亩地的秸秆卖出去,到手的钱不到100元。如果没人来收,还要自己雇车把秸秆运去回收点,每吨秸秆运费还得花上几十元。“农民算了这一笔账,觉得一点也不值。”周世丰说。
身在农村的王文石,看到了这其中的“商机”。两年来,困扰他的秸秆合作社的唯一问题是——“几乎没有盈利”。
成本,成本,还是成本!王文石脑子里有着一串将利润变成负号的数字——收一亩地的秸秆,搂草、打捆和运输,这一整套德国进口的设备,价格高达70万元。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大约300~400元,繁忙季节雇的工人必须24小时两班倒作业。每4亩麦田或每2亩稻田,可以收1吨秸秆,1吨秸秆运输百公里的费用是60~80元。
收来的秸秆卖给直燃发电厂的价格是200~230元一亩;卖给菌菇场作为蘑菇种植基料的是350元一吨;卖给造纸厂的话,秸秆质量要求更高,价格也稍高些,可达到400~500元一吨。“如果秸秆收得多,还能挣点儿。今年雨水多,收得少,可能要亏本。”王文石盘算着。
据周世丰介绍,由于中国的秸秆收集体系尚未健全,秸秆的收集成本较高,也影响到了秸秆制汽油乙醇的技术经济性。再加上,目前国家对于利用秸秆生产的纤维素乙醇还未有补贴政策,且油价走低,几乎所有国内燃料乙醇企业利润都受到了较大冲击,纷纷暂缓了各自的纤维素乙醇项目的开发计划。
他觉得,要推动秸秆制成乙醇的商业化,有一条出路——“给企业一块好肉的同时再给企业一块骨头”。
“骨头”就是,用秸秆制成乙醇的第二代纤维素乙醇技术。“好肉”就是,技术经济性更好的以粮食为原料的第一代粮食乙醇技术。2006年,国家叫停了玉米来源的燃料乙醇项目的审批。但周世丰认为,这一政策可以放开,不仅有利于消化陈化粮,还可以通过粮食乙醇和纤维素乙醇项目的共建,大规模降低单位投资成本。
出路,也是潘根兴必须考虑的问题,“用秸秆做成了肥料,谁来买呢?”
潘根兴决定试试这样一条出路是否有效:今年秋收后,他的团队作为一家企业的技术依托,将在北大荒农场上马一个项目。在像北大荒这样的地方,从秸秆收集,到加工,再到制成的生物碳化肥销售,整个流程都可以在农场内部的闭合链条内消化。潘根兴希望在这种模式下,把“收”和“卖”两端的问题一并解决了。
在王文石的计划中,未来也许会往田块更大、雨水更少的北方发展,效益可能会更好一些。“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这个农民出身的企业主相信市场的力量,他也期待,国家能针对秸秆问题推出更好、更精准的激励政策。
虽然今年能否回本还是个问题,他已经把秸秆合作社改名为“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
现在,他只能在一季接一季的秸秆大战遍地狼烟中,期待自己能守到云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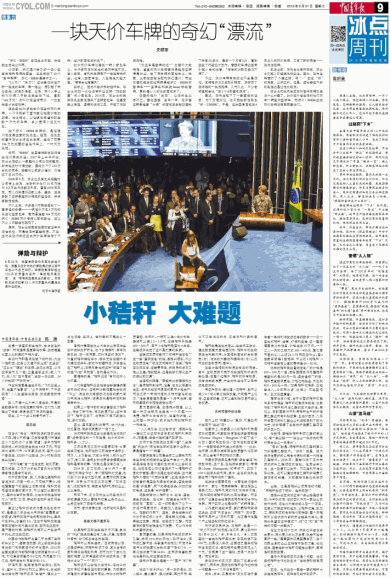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