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夜谭续记》正式出版,作者马识途已经106岁了,就此宣布封笔。和他同时代的作家——比如并称“蜀中五老”的巴金——早已成为历史人物,毕竟末代皇帝溥仪,也只比马识途大了9岁。
出生于20世纪初,活过了整个20世纪,21世纪又过去了20年,马识途的这辈子足够精彩。看着自己亲历过的“西南联大”“一二·九运动”“九·一八事变”,都成了教科书上的历史大事件,马识途仍在写作。
以1949年为时间分隔线,《夜谭续记》分为“夜谭旧记”和“夜谭新记”,还是四川十来个科员公余之暇,相聚蜗居,饮茶闲谈,摆龙门阵,仍是用四川人特有的方言土语,幽默诙谐的谈风,闲话四川的俚俗民风和逸闻趣事。
名为《夜谭续记》,是因为之前有一部《夜谭十记》,这一说,又是快40年前的事儿。1982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韦君宜向马识途发出邀约,用文字记录其“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异事”。
韦君宜和马识途是1937年冬在鄂豫皖苏区为湖北省委办的党训班的同学,还在白区一起做过地下工作,成为好友。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马识途曾以各种身份作为职业掩护,和社会的三教九流多有接触,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就像薄伽丘《十日谈》那样的格式搞出来。最终,10个故事结集为《夜谭十记》,1983年初版就印了20万册。
首战告捷,韦君宜和马识途都很高兴,商量着出一本《夜谭续记》。马识途都已经开始动笔写故事提纲,不料韦君宜突然中风,没人催稿了,这个写作计划一搁就是30年。渐渐地,连《夜谭十记》也淡出了新一代读者的视野,直到2010年,又发生一件事儿。
导演姜文将《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成为一时热门,作为原著小说的《夜谭十记》也重新红火起来。当时已经95岁的马识途想起了已逝的好友(韦君宜于2002年去世),脑子一热,决定重新动笔。
然而,这本书似乎注定命途多舛,开笔不久,马识途因癌症复发住进了医院。家人担心他的身体,马识途却想起了司马迁写《史记》,“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马识途让子女把稿纸带到医院继续写作,出院后也是一边积极治疗,一边坚持写作。当他完成初稿后,医生告诉他,他肺上那个肿瘤阴影竟然看不到了,查血指标也完全正常。此时,马识途104岁,宣布这是他最后的作品。
四川人的摆龙门阵,大概相当于东北人的唠嗑,北京人的侃大山,参与者往往都是社会平民。很容易让人想起《聊斋志异》,好故事果然都是聊出来的。
《夜谭续记》中的每个故事讲述者都给自己起了外号,不第秀才、羌江钓徒、山城走卒、野狐禅子……听名字就不是大人物,还透着那么点自认生不逢时;故事名为《狐精记》《树精记》《造人记》《借种记》《天谴记》……也不是宏大叙事的民间史诗,而是千百年来老百姓最爱围观的精怪、姻缘、因果。
当一个故事成为经典,总有后人想着将它升华,比如《聊斋志异》是抨击封建礼教和科举制度,揭露统治阶级残暴和对人民压迫——这么理解当然也没错,只是蒲先生当时未必想到了这么深。所以我觉得,作家写故事,不急升华,还是写个好故事要紧先。
“夜谭”系列是好故事:人神精怪并没有按着套路走,一不留神就是一个大转折;好人坏人并不分明,拧不过的只有时间,爱情有时圆满有时破灭,动辄就是一生,掩卷也只能轻叹。概括地说,马识途“不按常理出牌”。
比如,《狐精记》中,四川乡下一个富家二少,有些纨绔,去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念书只为光耀门楣,一点儿也不认真,还迷恋上了一个扬州舞女。看到这里,这是一个败家子的故事吗?不是。舞女劝说少爷好好念书,少爷居然听得劝,从大夏大学顺利毕业,因学业优异还成了大学教师,俩人终成一对佳偶。这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吗?不是。少爷的父亲去世,夫妻二人回乡奔丧,少爷的大哥却想独吞家产,于是一番争斗。这是一个宅斗的故事吗?不是。后来,还发生了少爷突然生病而亡,家中田产捐资助学,妻子也有了新的爱人……故事转折太多,如果要做阅读理解,真总结不出中心思想,却正像那个年代发生在那个地域的真实故事。
本来,故事里的事,也不是为了什么“意义”存在的。就像马识途评价自己的“夜谭”系列,“虽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聊以为茶余酒后,消磨闲暇之谈资,或亦有消痰化食、延年益寿之功效乎。读者幸勿以为稗官小说、野老曝言,未足以匡时救世而弃之若敝屣也”。
于《夜谭续记》,或许就是一个因为没人催稿而导致拖稿30多年的故事,告慰老友,以飨读者。中心思想不重要,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蒋肖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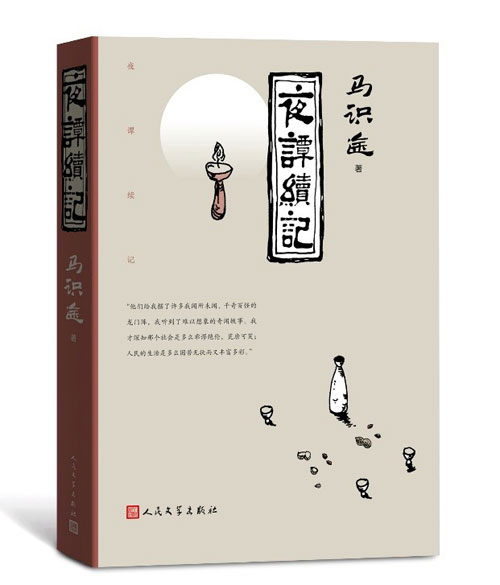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