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母亲荐我读的《伤逝》,再读一晃已是现时了。曾经我将莎士比亚的作品视为爱情的启蒙——浪漫是黑夜窗台下你的眼睛胜过20把利刃刺穿我心脏,永恒是我为你从冰冷的坟茔中醒来再一同长眠——但直到《伤逝》,我才有了极现实的关于爱情的思考;也是自此往后,我才从卡佛、从菲茨杰拉德、从塞林格的文字之间,读出那样“爱是想触碰却又缩回手”的小心翼翼和一颗真心。我们谈论的爱情啊,单是挂着“情”字,就足以告知人们其中必定免不了掺杂着人性本身的缺陷带来的不圆满甚至是丑恶,但也正因如此,其中那些真正伟大而诚挚的情感,才会愈发耀目。
我想我或许是能够体会母亲的用意了。
她所希望的,是我在仓皇去爱之前,先完成一个自由、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存在的认知,在爱和被爱的过程之中始终保持谦卑、平等,不断成长、臻于完善,而不是做一个被社会环境和观念所固化了的玩偶式的女性。我也曾暗想当年文青式的母亲,怎就嫁给了乏于甜言蜜语的父亲——但现在我明白,更有远见的的确是母亲,她没让极微末的生活抹平了她的意气,在长达20年的婚姻里,她塑造了一个温文而上进的伴侣。我想最理想的婚姻状态大概也莫过于此,仿佛松露巧克力,琐碎的日常是表面的可可粉,但恰到好处的正是这甜蜜与苦涩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的风味。听着电话里远在家乡小镇的父母叙说着他们怎样一同去看了不是太好的电影,怎样一起去湖边散步谈天消磨掉一个下午,甚至是怎样一起做了一道失败的菜品,我都会想起鲁迅先生借涓生之口所说的话——
“人生的要义,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哪怕是极微末的生活,哪怕是极微小的自我,也是一切爱的根基啊。
董蕴(21岁)中国科学院大学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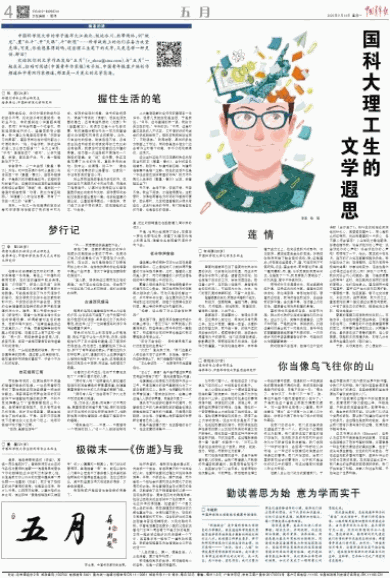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