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里曾经是祖孙三代8人一起过年的。后来大伯出国学习的几年里不能回家,再后来堂姐出嫁,祖父去世,我才慢慢怀念起过年的那些时光。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从小不善言辞,因此全家人团聚的时光于我而言,尽管现在想来温暖而令人安心,但当时反倒觉得漫长而无趣。如今回忆起20多年来的过年,竟发现记忆中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片段。比如过年早上恼人又让人期待的鞭炮声,团圆饭后照进卧室的一缕阳光——它们便是我对那些还称得上“团圆年”时的记忆。
祖父走后的这两年,我一直想逃避这些团聚的时刻,想忽视那些冲击着我神经的变化。我极力避免着在过年这一天突然涌现出过去发光的记忆,我尽力去无视周遭温暖的一切。
直到有一天坐在公交车上,一直没出校园的我看到街上那些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们,才突然感受到生命的热切。我看到有人在天桥上拍着桥下的车水马龙,看到有人对着公园的入口在吹着萨克斯,看到鼓楼的城墙外坐在一起的老人聊着过往,原来这才是生活本身最可爱的模样。
我倏忽间想到,原来过年,是犒劳我们辛劳一年的节日,是提醒一家人去热爱这些日日夜夜的时刻。这一天我们会怀念远行的人们,我们会回忆过去一年的岁月,更会期待接下来整整一年的温柔时光。我突然记起《寻梦环游记》里面的话,“也许我们无力阻挡时间的流逝,我们也必将与家人与爱人生死相隔。人类的记忆,便是对灵魂的延续。”
我发现我竟然期待起了过年。我开始和爱人讨论起年货,开始研究起年夜饭上饺子的馅料,开始期待奶奶除夕那天微信会给我转来的压岁钱,期待爱人的一手好菜。今年的北京,除夕万家灯火中应该会多亮起不少盏灯吧!其中的一盏下,有我靠在爱人的肩头,有他和我一起烧着饭。
李悦洋(27岁) 遗传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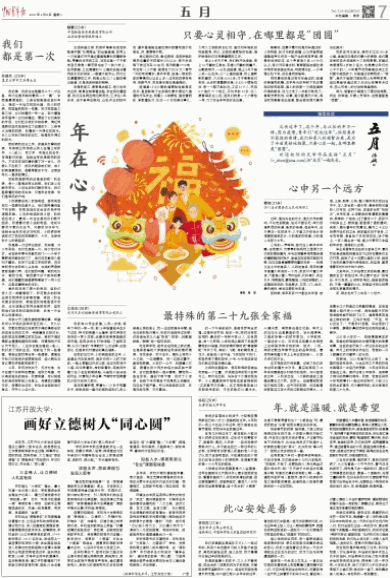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