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那年秋天,外公去世了。
我塞了张请假条回家,随即便在昏暗的老房子里看见了外公,他很安详地躺在那里。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的生命原来是这样的短暂,像一列火车飞驰而过,卷起路边一阵尘埃,尘埃在空中翻腾,又落下去,回到土壤之中,似乎没有来过。而死亡就藏在那飞驰而过的风里,不容易被人察觉——可它又是那样近。近得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五一”放假,我背着书包回到家里,妈妈正在吃饼干看手机,见我回来,抬头说了句“你奶奶去世了”。
奶奶和很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妇女一样,没读过什么书,不识字,十来岁就到了一个陌生村庄,嫁给了一个陌生男人,然后便开始履行所谓女人的义务——生孩子。奶奶一共为爷爷生了9个孩子,其中夭折了3个。
她一辈子都待在那个村庄里,日子冗长而单调,像织布机上的经纬,织出了那么多岁月的布匹,却全是一个花色,最后在数着土墙上光影的日子里一天天老去,将生命给予的一项项技能一一归还,最后一项,便是呼吸。
奶奶又是一位不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不会干很多活儿,做饭炒菜的事都是让爷爷做,对自己的小孩也是动辄打骂,从不关心他们这里衣服破了个洞,那里鞋子开了个眼儿。老了以后,逢年过节从不给小孩压岁钱,也不留大家吃饭。
去集市上赶集,奶奶从来是只吃不买,最后还同摆摊老板吵一架。问她为什么不给人家钱,她便两眼一瞪,手一挥,理直气壮道:“你们给我钱了吗!?”事实却是大家每年都会给。
奶奶还喜欢逢人就说子女们如何不关心自己,如何不给自己钱养老……
妈妈说,奶奶不会疼人。
三姑六婶说,奶奶自私又小气,跟掉到钱眼儿里一样。
左邻右舍说,奶奶好搬弄是非,不讲道理。
可我知道,奶奶不会疼小孩,奶奶自私又小气,奶奶不讲道理,全都是因为——奶奶自己就是小孩,一个老了的、任性的小孩。
我的故乡有座山,山下有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旁佝偻着两排已老了的樟树,奶奶有时会坐在樟树下的青石板上,和一群老太太一起卖菜,也不吆喝,只是那样坐着。
我有时经过那儿,总会犹豫该不该过去喊一声——因为奶奶是不认识我的,她有太多的儿孙了。有次我过去喊了,向她解释了很久我是谁,奶奶才终于想起来,然后便一面用她粗糙的手紧紧地拽着我,一面对其他买菜的老人们笑着说:“这是我孙女!这是我孙女!”
在我走时,她还塞给我一大把四季豆:“拿回去吃吧,拿回去吃!”于是我就抱着四季豆往家走。一路上长条的豆子们伴着我的脚步,一晃一晃的,像风在微笑。
后来,妈妈告诉我,奶奶每次卖不完的菜都会拿给她,不过,却是要付钱的。
奶奶偶尔会来我家吃饭。有次妈妈恰好有事不在,便由我来招待。我吃完后,一直心念着楼下的电视机。于是我犹豫片刻后,还是开了口:“奶奶……我下去看电视了?”
奶奶拿着碗筷,闻言转过头来,随即,我清楚地看到,奶奶那张爬满沟壑的脸上,原本熠熠的光彩一点一点黯淡下去,如老旧的灯丝耗尽了最后的生命般,嗞的一声熄灭了,只剩下一层厚厚的灰烬。冷风一吹便划开她的眼睛,飘洒进她眼里那片灰暗的原野上。
我几乎是待在原地,因为我在这样一片几近荒芜的原野里,窥见了一位迟暮老人的一生。
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到傍晚,奶奶会搬着她的小板凳,坐在夕阳下唱戏,唱来唱去永远是那么一段:“我十三岁嘞 就嫁给你爷爷嘞 早上去打柴嘞 下午去洗衣嘞……”
词曲都是她自己编的,方言里夹着戏腔,却没有丝毫吴侬软语之意,有的只是一个老人饱含岁月的沙哑嗓音,是如此的沧桑,是近乎让人落下泪来的凄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升日落所积攒起来的孤独和落寞。
奶奶是在一个早晨去世的,我上午才坐车赶回老屋。奶奶已经很老了,老成了这间土墙青瓦的一部分。早上在老屋后的园子里拔菜的,是奶奶;上午站在那口黑色大铁锅前炒菜的,也是奶奶;中午坐在那张脏得已看不出原始色的八仙桌上吃饭的,傍晚坐在门前的矮石梯上望着夕阳发呆的,晚上躺在昏黄灯光下回忆往年的……全都是奶奶。老屋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方凹凸不平的土地上,都有一个或站或坐着的奶奶。
妈妈让我去给奶奶作个揖,好让她保佑我考个好大学,我是向来不太信这些的,一个人生前做不到的事,死后反而就能做到了吗?但我还是去拜了三拜,不是为她保佑我,而是为了别的。
奶奶下葬那天我没能去,因为我还要上学,妈妈不让我请假回来,所以我当天晚上就又坐车离开了。我走时是在晚上,茫茫夜色之中,我看见板凳上和矮石梯上的奶奶站着门口目送我离去,她渐渐地融到村庄的黑暗里。远处的狗吠声此起彼伏,我再也看不见奶奶了。
(指导老师:刘剑)
彭妍 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高二716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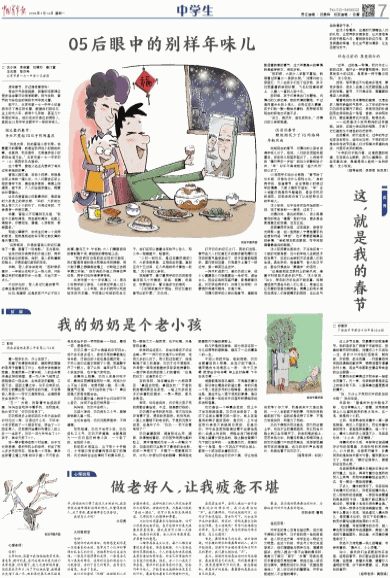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