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石婆婆5点就醒了,蓝色的阳光涌在窗台,她老了,容易察觉天亮和雨天。孙子睡在对面的房间,房门紧闭着,他的闹钟已经开始响了,听了3年的咚咚锵锵,都是类似的噪声,刚好5点半。她支撑起腰身,那块折断的腰骨即便手术后如今灌好了水泥,却依然凹陷了下去,在刮风下雨的日子里刺刺地疼。
“嗐!”孙子起床了,他弄掉了手机。这是现在的年轻人爱说的一种感叹,阿石婆婆常常听不懂孙子从大城市“带”回来的语言。孙子说打算考研了,阿石婆婆知道很多小孩都能考上研究生,赚大钱。于是第一年阿石婆婆便在考虑明年该怎么跟亲戚朋友夸自己的研究生孙子。孙子读的是什么学校,她其实到现在还不清楚,但女儿告诉她孙子都毕业了。第二年,阿石婆婆打算跟亲戚说自己的孙子其实用了一年时间准备,现在才开始发力呢!他每夜辛辛苦苦地看电脑,现在的孩子用脑去学习可辛苦咯,以前放学回家都黑黑瘦瘦的。第三年,她每天焦急地坐在店里,双手紧抓椅子的把手,神色凝然,唇和肥厚的下巴紧紧地塌着,仿佛一位临政的皇太后,各色说辞在舌头上滚了一遍又一遍,热气腾腾地呼出了一番却总不满地又重新嚼回去。这只老骆驼恐惧地在女婿的店里头坐着,眼瞅着店门口那片晒得白晃晃的马路。孩子学习总归是辛苦的,不能太累了,可她还是昂首望着马路,她知道她想盼的盼不来,但还是不能懈怠,孩子在家里关着房门学习可累了。
这个早晨阿石婆婆像往日那样拿着一张小红凳,拄着那条光秃秃的竹竿,那是孙子上大学前帮她削好的——他知道外婆疼他,他也知道阿石婆婆不爱那种拐杖,她老了,但还是爱美的,趿着的那双胶拖鞋依然是粉色的,要么就是明亮的油饼黄。
大朴树的叶垂坠着,滴答着彻夜的温凉,太阳萎靡在树梢下,光一圈一圈温顺地汪出来。昨晚打了闷雷,雨水积在半空却肠痛一样,死活无法泻个痛快,细细密密地洒了半空,空气里闷足了水,和着白日里残留的郁热,把土里的臭虫和蜘蛛都逼了出来。
阿石婆婆出门时就听到孙子起床的声音,放音乐然后摇晃床板。她好不容易拖着腿脚来到小区门口坐下,看走过路过的行人和车辆,等女儿来接她去店里。女儿和女婿就是靠这个杂货店为生的,她要看着他们在店里忙乎才放心,这路上车多人多,不小心撞着磕着都使她放心不下来。
“嘟嘟嘟”怀里的手机响了,手机是孙子给她买的老人款,字大声响,她掏出来,只见屏幕上明晃晃地写着孙子的名字,她摁下接听。“喂,婆婆,老妈说她去市场买菜,可能会迟点接您,您……”阿石婆婆眼睛还没完全花掉,她在听电话的时候,看到孙子从小区门口举着电话走出来,依然是那一身高中的校服,高高的个子,白茫茫的脸。她激动地拄起竹竿,喊道:“言仔!”他拿着电话似是听不到,头也不回地往另一方向走去。
她赶忙拿起电话问孙子。“言仔,婆婆叫你你怎么不听呢。”“婆婆,老妈说她去市场买菜,可能会迟点接您,您坐在小区门口等她一下……婆婆,老妈说她去市场买菜,可能会迟点接您……”孙子一直重复着话语,阿石婆婆说的话他仿佛一句都没听到,最后他挂掉了电话。年轻人,真的是古灵精怪,阿石婆婆想着。
女儿车筐里装着满满的菜,在刹车的时候差点都扶不稳车头。阿石婆婆说孙子穿着校服从家里跑出去了,打电话也说不明白。女儿没有回答,眼睛湿润地盯着前方,车在红绿灯前停下,耳机里传出儿子的声音,“妈妈,现在是红灯,距离店铺还有880米,红灯还有36秒,我知道妈妈最近的风湿又犯了,但腿还是要踩好,让婆婆扶稳后座哦。”
房间里床铺与书桌上都铺满了灰尘,一件雪白的校服挂在衣柜外面。书桌上有一个手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启动感应、定时、播放和发送的功能。
骆力言(23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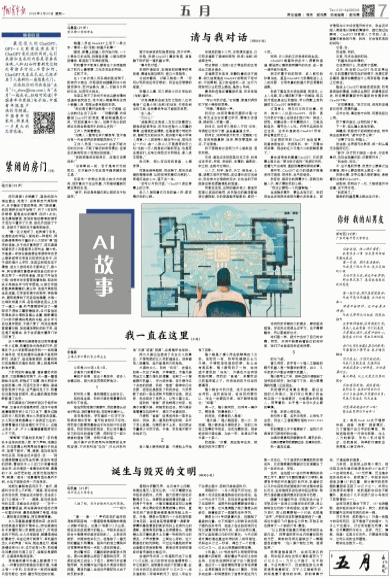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