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某天,茶花用手扒开被烟火烧燎过的茶丛,乱枝残叶下,露出黑漆漆的枪杆。
她对上飘摇风雨中从此无法割舍的一眼。
茶花把人带回了家,那是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少年。
茶花的父亲连着抛出好几个问题试图探明少年的来路,但对方只是怔怔地回望他们。
“吓丢了魂,身上又背着枪,逃兵,懦弱的逃兵。”父亲做着结论,无奈地叹气。
“逃兵”二字刚一出口,少年激动起来,他似疯了一样,流着泪,在挣扎什么。
茶花见此情景,愤慨的心又遭怜悯浇凉。动荡年代,人人都守一身易摧易折的肉躯,无归处地匍匐着,她开不了口去指责谁。
茶花靠近少年,问:“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的脑袋像被撞过的钟,耳边长鸣着。他看着茶花的双眼,迟疑地在她的手掌上画出3个字:杨湛生。
杨湛生生于北方,因为战乱随家人一路南下。几千里漫漫长路,几度磨穿了他的皮肤,也磨走了他的血肉至亲。
决定安静等待死亡的那日,他被一支要南下去边境的队伍收留。那些人告诉他,带他去修公路,修好了公路,国际支援就进得来,鬼子就打得过,百姓就能挺过这场苦难。
杨湛生重新振作起来,像隔年春天永远能再见的绿芽。
可是路仍然不好走,敌军的偷袭迫使杨湛生和队伍分开。他再次变成一个人,无助地奔跑在到处都找不到遮蔽的大地上,直到藏身的茶丛被茶花拨开。
茶花和父亲收留了杨湛生。他们互相依靠,搭建起一个家。
每天父亲都会背上竹筐出去行医或采药,换来不多的食物维持生计,而茶花和杨湛生则守着几处奄奄一息的土地和努力撑立的茶丛。他们运水,耕种,挑挑拣拣,延续硝烟散去后还未灭的希望。
茶花一家是被宗族血脉捆住的人,任凭猩红和刀枪无情,只守一亩三分地,只盼来日光明路,恪守着“生”与“活”二字。
杨湛生起初并不适应,他躲过无数大小地方。他怕,怕守在一处终会迎来滚烫的烈火。
可当茶花带着他去到河边,看那些未被灼烧过的繁花,听侥幸存活的山雀发出动人余音。她用手捧起水,替他清洗过脸庞,含着乡音呢喃着:“洗洗水,岁岁好,杨湛生来年,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茶花重复了两遍,这是乱世中最昂贵的祝福。
水划过他的脸,好似有泪。杨湛生想,多奇怪,不见天日的灰蒙中,他也能寻得仰头可见的光。
从此他心里升起一座碑,碑上刻着他一生的念。
他想对茶花说点什么,好像是关于爱的字眼,喉咙却不起作用。
宁静无长,在某个落日余晖消散干净的傍晚,茶花没有等到父亲。杨湛生拉着茶花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终于,在某片烟火尚未飘尽的枯枝杂叶覆盖处找到了。
茶花父亲一生行医,拼凑起他人,自己则落得七零八落的结局。
茶花心里恨,可恨像高高抛起的石块落尽深洞,好久听不到响,憋得人几近窒息。
那晚,他们顶着无尽的黑埋葬了父亲,等待天明的过程诡异地被拉长。茶花躲在杨湛生的怀里,变回只会号啕大哭的婴孩,阵阵如哀歌,声声如啼血。
杨湛生张了张口,像是想吐露关于安慰的字眼、关于许诺的誓言,但他还是发不出一声。
此后,杨湛生一瞬间从少年长成了青年,他的肩膀依旧消瘦,但扛起了茶花所剩下的一切。
陈旧的耕具捆住麻绳,再拴在杨湛生身上,他们一步一脚印,在满目疮痍之上拖拉出生存的信号。
似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命运悄悄背过身去。连着许久,日子安定。
木桌上渐渐有了难见的丰盛,几颗煮得软烂的土豆,几片烫水的白菜。窗外是圆满的月亮,皎洁无瑕不食人间危难。
茶花忽然泪满眼眶,她不禁低头言语,许下极其微小的愿望,只求这样安稳,日日夜夜。
杨湛生扯了扯嗓子,虽仍不能言,但在心中已经跪拜这破败潦倒的天地千万次。
人之美愿,好似仅能维持几息。
杨湛生心里始终畏惧的烈火还是砸向了这里。他跪在地上任凭掉落的碎片如暴雨倾下,拼命从废墟里拖出了茶花。此时此刻,茶花真如枯萎一般,歪着头,半睁眼,勉强呼吸着。
杨湛生将她安置在隐蔽处,用手慌忙地比划着:我会很快回来。茶花轻轻眨眼,作为回应。
我会回来。他再比划了一遍。
杨湛生跑在曾经熟悉的山野,浓烟四起疯狂灌入鼻腔,他分不清咳的是血还是泪。迷蒙间,他撞见了一支军队,顿时方寸大乱。
“你是谁!哪里来的!”对方举起枪瞄准他。
他说不出话,卑微地弓着身体,做着哀求状。
“别开枪!好像是自己人!”有人接话道。
他们朝杨湛生走来,拉住了他。杨湛生不肯,他疯狂挣扎和比划着,那双猩红的眼投向每个人,他要回去。
可没人懂得,无人知晓他不能言的感情。
他们带走了杨湛生。
杨湛生的哭声与紧跟而来的轰炸声融为一体,他呆滞转头,那处只有他知道的地方升起了火光。
……
1949年,从数场大小战役中走出的杨湛生挤在兴奋的人群中,听到那句苦尽甘来的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人声鼎沸之下,他反复摩挲着心中那个遗憾的角落。
1952年,杨湛生跟随军队往北方走去。这个用半生南下的人终于回归北方。
朝鲜的雪比家乡的苦涩不少,他倒下时,竟被苦出了眼泪。
身边战友不停呼喊他的名字,可眼前不停旋转的天地竟让他觉得异常舒适,他想睡去了。
“哥!”那个一直跟随他的小兵大叫着。
杨湛生支吾一声,感觉在硝烟中闻到了茶花香。
“哥!你说什么!你再坚持一下!我求求你了!”小兵哭着,和多年前的他很像。
杨湛生想了很久,鼻间萦绕的茶花香愈发浓烈。
他努力仰头,拼死脱口一句:“我……不是逃兵,我没有逃走过……”
任何时候都没有逃走过。这是他未说尽的话。
杨湛生呼吸停止的瞬间,在新中国的大地上,茶花曾经倒下的地方,有人撒下了新的种子。
冯嘉美(2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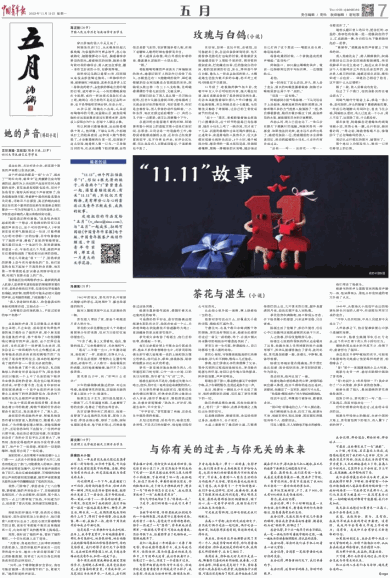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