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江南六月的夜,清朗的月高高挂在黛黑色的天空。镇上家家户户都亮起了橘红色的灯,那灯光如萤火般微弱,这儿密那儿稀,朦朦胧胧。这里的灯光没有大城市炫彩霓虹灯的五颜六色,光彩夺目,它们简简单单,爽爽朗朗,清清白白,一如生活在这儿的人们。吃饭穿衣,养家糊口,别的无有。这里夜并不安静,那鸣蝉在暗处的高树上嘶吼,大声喧哗,那蛙声在田野里起伏阵阵,搅动着空气中骚动的热气流。谁家屋前小广场放着动感的流行曲,妇女们扭着身体,和着旋律;有的老人坐在屋檐下,穿着肥裤大衫,时而摇动手中的蒲扇,你一言我一语,聊得眉飞色舞,笑声阵阵;还有那娴熟的颠锅声,那锅与大铁勺的碰撞声清脆悦耳,底下的焰火,张着大口,散出热,发出光,映红了小贩那忙碌与沧桑的脸庞,汗不住地往下坠,手不停地翻动,蒸笼的热气不断升腾,氤氲着温暖的味道。
其根照常下了晚自习,拖着经历一天学习的疲沓躯体,穿过兜兜转转的巷子。刚从闷热的教室中出来,他有点烦躁,浑身黏黏湿湿,一股汗臭味,尤其是感觉有千万只毛虫在头皮上密密麻麻地蠕动,头发缝里又湿又热,感觉有一团热气在头上挥之不去。终于到家了,奶奶躺在躺椅上,摇着蒲扇,听见其根的脚步声,立马摸黑冲到门口给他开门,打亮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小电灯,门开后,其根便双手举高,一翻,把短袖给脱掉了,灌了好几杯水进肚子,有点疑惑,问:“奶奶,今天的水怎么有股腥味啊!不太好喝!”
奶奶边拿其根洗澡要换的衣服边说:“你小子,嘴真刁,一点味道都能试出来,哼哼,这是我在这条街上头的压水井里打的,我明天再找几个大的塑料瓶子去打上几瓶,省得我还得用煤气去烧水,不知道要烧多少钱!”其根忙接着反驳:“别啊!这镇上的水不像咱家的,那是被污染的水,是喝不得的!”奶奶急了:“你懂什么,那么多人都从那里打水,也没见谁吃出什么毛病来啊!就你话多,读书读得越来越娇生惯养了啊!”其根不说话了,拿过衣物,提着后阳台上晒的水进卫生间洗澡了,这水弄到身上冰凉冰凉的。
时间慢慢走过,四周也渐静了,其根洗完澡后感觉一天的燥热也洗得差不多了,走过后阳台感觉风也是凉爽的。那小窗还亮着橘黄的灯光,十分微弱,他知道,那是奶奶为他留的。他凑过那窗,看见奶奶还坐在床上,勾着头,两眼微闭似睡非睡,不时还有微微打呼声。不知为何,其根发现奶奶的白发在此刻是那么显眼,如雪如霜,脸色也十分憔悴,那皱纹布满了额头、眼角,脸庞……还有那粗糙的老手起了多少茧子,厚实的指甲藏了多少泥垢?其根的眼眶有点红、湿湿的,嘴里感觉有股涩味,就像小时候嚼的那些野草梗子的味道。
这时奶奶突然惊醒,见其根还没回房间,扯起了她的嗓子大喊:“根崽,你在做什么啊?洗个澡洗了这么久!以后在人家手下干活,这样是没有饭吃的!”其根在窗前以寻常的口气回应:“哎,你真啰唆,我这不是洗完了吗?”
说着便进屋了,刚准备躺下睡觉,奶奶便下床,神秘兮兮又有一丝得意地说:“你先莫忙睡觉,我有样东西给你!”说着便从墙面的挂钩上取下一个袋子来送到其根手里,“这是楼下的老板娘子卖剩下的发糕,晚上纳凉时她就每人分了几块,我拿在手上没吃,想着留给你吃,你下课估计也饿了,快把它吃了吧!”其根接过发糕便拈了一块送到奶奶嘴边说:“你也吃一块吧!快!把它吃了!”奶奶把嘴撇到一边:“你自己吃,我血糖高,不能吃甜的,别磨磨蹭蹭了,吃完赶紧把灯关了,灯照了这么久,不知道要交多少电费了。”
其根放弃了,自己吃了起来,甜甜的,有股大米的清香,嚼在嘴里软软的很有嚼劲。奶奶微笑着看着其根吃发糕,调侃道:“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你以后要是考上了大学坐办公室,一定要寄钱给我用,买吃的给我,要是不给,我可是要向你讨的!”其根故意反向应和着:“我就是不寄钱给你,而且还不回家,你敢坐火车找我吗?你可是一辈子都没坐过火车,还是坐汽车都会吐的人哦!”奶奶假装生气说:“哼,我有一张嘴,到时候我见人就说我养了一个白眼狼孙子,说你怎样没良心,你就会被村里人骂得狗血淋头!”说完,奶奶已经躺床上了。其根狼吞虎咽吃完那两块发糕后也躺下了,听到奶奶嘴里还在嘀咕着:“这次我们欠了老板娘子一个人情,吃了人家的不能不还,下次回家,我要摘几斤辣椒、黄瓜、茄子给她,再掐几斤仙草给她,让她做做仙草豆腐吃吃……”
房间里的灯熄了,只剩细微的呼吸声、床板的咯吱声、老鼠的吱吱声……又一个夜晚过去了,其根也不知道这样的夜晚还要过多少个,还有多少个。
甘柳(24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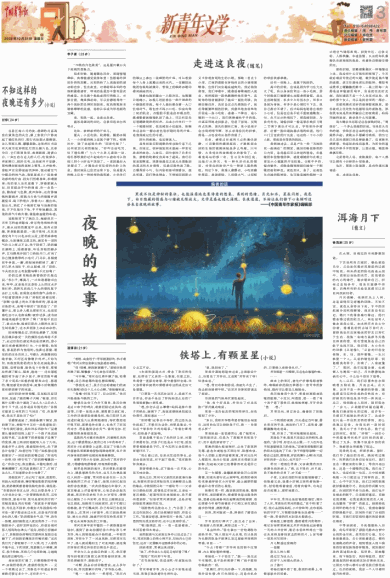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