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红打定主意要和三杰分手。
那一年晓红19岁。她是干部家庭出身,父母都是党员,三杰只有一个爸,老头儿到60岁还没个正式工作。晓红高中毕业,三杰初中就进了工厂。晓红考大学失手,被分到厂里,那也是文艺骨干、仙女、厂花独一朵。三杰不过是大几百名没主男工人里的一个。
因为一次合唱,二人相识。“然后竟在一起吃过三次饭!”晓红嚷嚷,“我怎么这么傻!”后来大家纷纷传言他俩好上了,晓红想,谁要跟他啊,赶紧说清楚。
其实不需要说。晓红坐在凳子上沉默,三杰伺候在旁,不敢吭声。半晌晓红说,我想说什么,你都知道了吧。三杰说,是。
又沉默了一阵,晓红要走。三杰送她到院门口,紧跟着,还不说话。晓红心一软,转身问,“你想留我?”三杰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我不敢想。”
愣了几秒,三杰抬起头来问,你饿不饿?
所以他们吃了第四顿饭。和前三顿一样,三杰掌勺,每个菜都让晓红惊喜。
红爸意气风发时恰逢变动,被送去农场“受教育”,红妈带着三个孩子,忍气吞声地熬生活。所以在晓红的记忆里,年轻的胃总是空空的,偶尔吃个白水煮蛋,已是大不易,还侈谈什么滋味。生活磨砺,红妈渐渐没了柔情,做事果毅,对晓红说话简洁、清晰,都用简短的命令句,“去寄信”、“看好鸡”之类。
那几只鸡就养在院子里,晓红负责每天收蛋、清点。后来鸡老了,红妈杀了煮汤,清汤如水,多分出来的一勺,添给晓红。
三杰虽然早没了妈,但有四个姐姐,在吃不饱的日子里,他也不缺疼爱。等后来拿了工资,他变着花样儿买些食材练手,手艺渐长,变成全家最会做菜的人。
给晓红做菜,三杰花样百出。那个年代,小城没有南方的新鲜菠萝,只有软烂的糖水菠萝罐头,三杰一次买好几瓶,只取菠萝芯,改刀成圆柱形细长条,口感才脆韧。红烧牛肉早就炖在砂锅里,半筋半肉,一看就费尽心思。
吃这样的菜,晓红能找到那种期盼已久的受宠感觉,很陌生,很受用。
三杰最拿手的一招是熬鸡汤,晓红从没见过的白色鸡汤。她总以为,只有骨汤、鱼汤是雪白的,鸡汤就是再鲜,也状如清水。但三杰熬的鸡汤,不知熬了多久,竟也能变成白色,影影绰绰看不见底,只见到黄灿灿的鸡油花飘在上面,随着勺子拨弄,分分合合。
喝完两碗鸡汤,听三杰说些有的没的,不知怎么,分手的话题就算揭过去了。
过了一阵子,晓红又提分手。这回说出了好几条充分理由:三杰学历拿不出手,长相带不回家,婚礼都不知怎么办,两人平时没什么共同语言,还怎么过一辈子?!
三杰讷讷无语。半晌问晓红:你饿不饿……
“别跟我提吃的!”晓红意志坚定,拒绝诱惑。
“我怕,以后你跟你妈,都喝不到我熬的汤了……”三杰轻声说。
晓红心里一动。这次分手计划,又糊里糊涂地揭过去了。
厂花和穷小子的结合,最终熬过了女方父母亲戚们激烈地反对,熬过了一干人等的大跌眼镜、语重心长,就像一锅鸡汤,由清到浓,不知哪味料起了作用,竟是熬成了。
婚礼那天,三杰兴奋至极,执着晓红的手,许诺说“这一辈子我都做饭,只做给你吃”。晓红通体酥软,好像是那渴望已久的专宠滋味,能够让人融化。
婚后第一年,晓红家给他们买房。人们去贺喜,见到三杰忙里忙外,晓红十指不沾阳春水。“她被宠上了头!”有人悄悄议论,“三杰这是入赘了?”
晓红扬着下巴,笑着瞥一眼,不作解释。三杰不说话,转身进了厨房。
婚后第二年,晓红生了女儿。三杰开始喝酒,下厨也少了。有一次醉中吵闹,三杰扬手一个耳光,晓红耳膜穿孔。
晓红没告诉任何人。红妈问为什么最近不回娘家,她也对付过去,“当初铁了心,是我傻,所以自作自受,说不得。”
况且她以为,三杰是一时犯了混。从医院回来,一碗白色鸡汤端到她嘴边,醇厚如昔,三杰高举汤碗,手微微颤抖,紧张地说不出话来。晓红眼眶湿了,也没再多话。
日后混事竟越来越多。许多次,晓红眼眶乌青,出不了门。而这种时候,三杰才会回归“正常”,回到当年那个无话、“老实”的样子。那份温存、暧昧、黏黏糊糊、战战兢兢,是晓红似乎永远也瞧不上,又怎么也离不开的感觉。为了这种说不出的感觉,那些明摆着的错,晓红也假装看不见。
时间久了,很多话旧到不能提。还记得那句“一辈子做饭”吗?女儿12岁的时候,三杰在外面有了另一个家,有了儿子,他抱着儿子走了。晓红和女儿这一辈子,不可能指望吃三杰做的饭。
为了女儿,晓红做饭、煮汤。她翻遍了所有菜谱,把老母鸡用小火熬了整夜,那汤滋味足够,却总是清得一眼见底,就像是火候和心思还不到位,“不知道他煮了多久”。
直到女儿成人,晓红也没有新的归宿。有一天,她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看见,所谓的白色肉汤,是油和水混合翻滚而成,油脂多肉,比如煎过的鱼和猪蹄,汤色如奶。鸡汤颜色本应清澈,如果想变白,就另外加油煎,或者放几片淮山。电视里,厨师现场演示,不到两个小时,一锅白色鸡汤就熬好了。
年过半百的晓红终于弄懂了熬汤。原来,那些看起来醇厚浓郁的汤,那些听上去满怀深情的语言,未必真是经过了时间的熬煮,有时一两勺催化剂,让人忘记本真,迷失在幻想中,误以为那才是渴望已久的滋味。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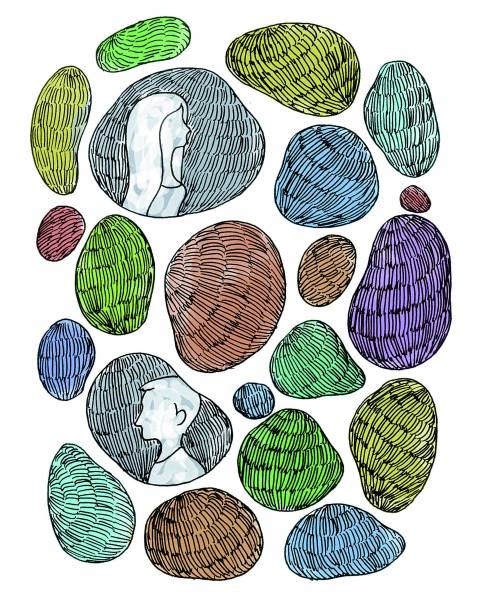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