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川越过茫茫沙丘,蜿蜒过数条潺潺溪流,孤寂地散落着不多的人家。在这个叫作安溪镇的地方有个破破落落的茶园,叫作安溪茶园。安溪茶园种着百亩茶田,却从不贩茶。但安溪镇的居民只做一件事,种茶。
陆十七也不知道这茶园有多少个年头了,从他有记忆起茶园就已是破破落落的模样了。外婆总是摇着蒲扇在他耳边念叨:“茶园茶园,故园故园。丢了茶园,丢了故园……”
他知道茶园,却不知道什么叫作故园。也许是茶梗上的一抹绿色,也许是茶田一眼望不到边的孤寂,也许是穿梭其中凌乱落寞的风。
他也从不去想,他只如小镇上那些匆匆忙忙在日月交替中完成一项又一项循环的村民们一样,仔细劳作,分辨着春茶、头采茶、头春茶、明前茶和雨前茶。外婆教他,立春后到谷雨前采摘的茶叶是春茶;茶园开园后,极少量采摘的茶叶是头采茶;第一波春天采摘的茶叶,是头春茶;清明节前采摘的茶叶是明前茶;清明到谷雨之间采摘的茶叶是雨前茶。
外婆好像什么都懂,又好像什么都不懂。
她知道关于茶园的一切,却不知道茶园外面的一切。
陆十七跑出去过,因为打翻了一碗莲藕粥和外婆置气,偷偷收拾了行李发誓要跑出这个破落茶园。他拖着笨重的包裹向着茶园左岸跑,他想,只要跑出这座茶园,就能脱下那裹挟于身的命运。
可是,人是永远也无法与故土割舍下联系的,这道理陆十七早就懂了。他刚跑出去一天,就因饥饿与疲倦交织又折返回茶园。外婆见他回来,眼里涌满晶莹的泪花,一把将他抱在怀里,让他差点喘不过气。晚上外婆小心翼翼地问:“十七,茶园外边是什么呀……”陆十七大口咬着刚烙的面饼,嘟囔道:“茶园外边呀,可好了!有一幢一幢的高楼,有一晚上都不灭的霓虹灯,还有吃不完的新奇糕点……”
过了很多年,陆十七都没忘记那晚外婆的神情,她瘦弱的身躯靠在窗棂上,蜡灯微弱的光晕染在脸庞上,凝结出无数朵孤愁。
外婆其实也是想出去的吧,她会向过往的行人打听外面的世界,会在每年春风起的时候放一只高高的纸鸢。可是,当时的陆十七不懂。他只知道,外婆会极其重视当季首次采摘茶叶的祭拜仪式,开山祭茶、奉贡果,燃清香。跟随人群中整齐而坚定的语调,齐声高喊:
“一鞠躬!愿神灵庇佑!”
“再鞠躬!愿风调雨顺!”
“三鞠躬!愿施恩降福!”
陆十七也跟着弯腰鞠躬,跟着闭目祈福。他恍惚中觉得安溪镇似乎永远会与安溪茶园盘根依缠,久久矗立。外婆也永远会在安溪茶园里护佑他长大,直至他长出羽翼飞出这片茶园,再也不会回来。命运的戏剧性就在于,在他暗下决心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时候,外婆却永远不会回来了。外婆葬在了安溪茶园里,在此长眠的还有遇难的陆十七父母和安溪镇的几十个村民。
陆十七捧着花圈,透过遗落在茶田上的祭酒珠滴,目光被折射得很远很远。远到看见那场罕见的山体滑坡,将他的父母、他的叔叔婶婶们淹没进去,直至没过整个身子消失不见。他的心脏仿佛被穿透了一个洞,让他开始急剧地想逃离这片故土。
安溪镇从来不贩茶,而安溪茶园从来也只种茶。
他曾问外婆,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的茶却不卖出去?为什么安溪镇的居民从来都不会向往外面的世界?为什么每年都要举办这么冗长的祭祀仪式?为什么安溪茶园的牌匾永远都是那样破落却不翻新?……
外婆爬满皱纹的嘴角微微地翘起,轻轻拍着他的背告诉他,很多事情都是没有答案的——抬着头往前走,遇到什么就接受什么。人这一生,慢慢熬着一辈子就过去了,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外婆的回答太过隐晦,陆十七实在听不明白,便也抛之脑后了。
他回过神,久久凝望着这片广袤而望不到边的茶田,晚霞的余晖斑斑点点投撒在每一片茶叶上,与身后长眠的亲魂融为一片。他似乎在那一瞬间想明白了些什么,又想通了些什么,唇间挂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向着茶园左岸走去。
安溪镇只种茶,安溪茶园破落的牌匾,安溪茶园每年冗长的祭祀仪式,安溪镇从不向往外面世界的居民,都是因为茶园土地下有无法相见的亲人与无法割舍的故土吧!外婆放飞的每一只纸鸢,都是因为她的小孙子向往外面的世界。她向过往的行人打听一些事情记在心里,回家讲给小孙子听,他便不会想着要离开了吧!
可是,外婆不知道的是,他那天没有跑出去茶园。
茶园左岸,还是茶园。
宋晗(22岁) 兰州工商学院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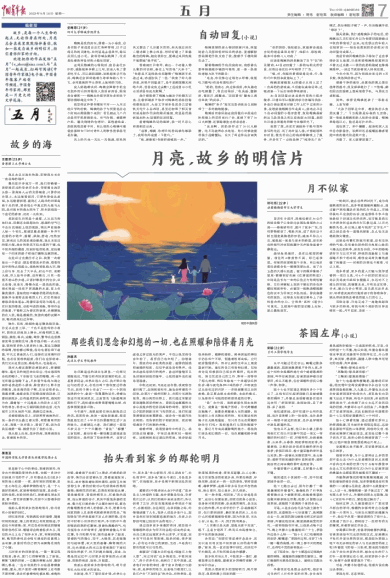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