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白河滩,就是石桥村。
班车没有规律地一颠一簸,一点一滴地磨掉车厢里回乡的人们的热情。
边杰没有热情。晃晃荡荡半袋子胃酸,伴着没消化的午饭,随着车厢抬升砸落。为了不浇灭车厢里仅剩的热情,边杰决定半路下车走回家。
边杰3年没回村了。自从上了大学,一个崭新的、精致的世界向他展开。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边杰兴奋之余,又带着一丝畏怯——怕被同龄人闻出自己身上的泥土味。不过,好在他的姓氏给他带来了便利。不常见的“边”姓,给同学带来了新奇感,边杰也顺道挤进了新世界。
3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边杰还沉浸在新世界的探索之时,父亲的一通电话打碎了他的美梦:“再不回家过年,就断了你的生活费。”
边杰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就像飞上天的风筝,飞得再高,线头总还在父亲手里。仓促收拾好几件换洗衣物,赶在除夕前一天,边杰赶回了家。
农村建房子,总是靠着大路。
城市的路给房子带来的是喧闹,农村的路给房子带来的是热闹。
边杰的家也靠着大路,是一栋三层小洋房。一楼是大厅和父母的房间,外加一个小矮楼作为厨房。二楼则留给了边文、边武和边杰3个儿子住。随着大哥和二哥成家出门,准备立业,边杰在外3年,二楼也就空了3年。至于三楼,就是一个架子,空空荡荡,也没装修。
村里讲究排场,人家建三层,我也建三层,谁也不比谁差。
三楼的房间没糊腻子,露出里面的红泥砖头,像被剥开的皮肉。伴着一年又一年的爆竹声声,结成一道所有人都淡忘了的疤。
下车好一会儿,边杰才从晕车里缓过来。周围的山垄田地看着陌生,新修的路弯弯绕绕。边杰靠着手机导航,总算是找到了回家的路。
到了院门口,父亲靠在大门旁边,正坐在小竹椅上。听见动静,父亲朝着门口望来,眉毛蜷在一起,在额头像是打了个结,看了两三秒,才缓缓舒开,而后又拧巴在一起,把头转向另一边。边杰拎着行李箱,缓步走到父亲旁边,小声叫了一句“爸”,就快步走进屋里。
母亲是在傍晚才知道边杰回家了的。打开房门就是一通数落,不外乎是一些不要爹妈、不要家的话,边杰在电话里已经听过好多遍了。在外3年,边杰学会了如何应对母亲的啰嗦——只要静静地听着,听着就好,这种沉默,带着某种反抗,又带着某种怜悯。讲了一箩筐,母亲看边杰也没个声响,丢下一句“晚上记得去你萍姐家订婚宴”就走了。
石桥村基本都姓边,村里头大家或多或少都可以算上亲戚关系。萍姐叫边萍,就住在隔壁,是边杰儿时在村里为数不多的玩伴,边杰总喜欢围着她转。但过了几年,边杰发现自己不过是一颗卫星,萍姐终归还是找到了她的太阳。
农村的婚礼总是扎堆在春节前后,也只有这个时间,才有足够的人手可以帮忙。
订婚宴是在祠堂举办的。边杰到祠堂的时候,宴席已经开始了。刚落座,正想埋头扒饭,旁边一个大姨就认出他来了。
“这不村头老洪头家的阿杰嘛,啥时候到家的啊?”
一口夹杂了半嘴红烧肉的家乡话,边杰咀嚼了一下才听明白。老洪头就是他父亲,边洪,在村里头同一辈分里年龄最大。
“姨姨好,是的,刚回家。”
见到女性长辈叫姨姨,见到男性长辈叫叔叔,这是边杰在无数次记不清是哪个亲戚后,总结下来的经验。
“孩子真俊啊,读书还好。当年考上大学,老洪头满村报喜来着呢,逢人就聊,半句话不离这孩子。”大姨把话围桌传了一圈,像是发现了一个稀罕物件,同桌的人也乐得有了谈资。还有一个看起来更大的姨姨,一拍头,说小时候还帮他把过尿呢。
突然成为焦点,让边杰有点坐立不安,只能嗯嗯啊啊地应付着这些不熟的亲友们。
“这孩子,还真是进了城就忘了自己哪来的了。”
“那可不,他和咱可不一样,名牌大学生,有出息着呢。”
“没记错的话,这娃3年都没回村吧,不知道的以为是回家旅游来了呢。”
“老洪头这怕是表面风光心里苦哟。”
……
窸窸窣窣的话顺着桌面漫过来,边杰只能就着一大口菜,一起咽下去。
宴席中场,萍姐和她的未婚夫向宾客们敬酒。边杰远远地看着那张陌生的脸,总和记忆中的她对不上。她像一棵催熟的油菜花,带着一种过分的明艳和臃肿。赶在敬酒到这桌前,边杰就悄悄地走了。
回到家,父亲还在院里,坐在小竹椅上。“回来了?”“嗯。”
父亲右手搭在膝盖上,仰着头,看着边杰。边杰就定在原地。
那一弯月亮挂在夜空中,旁边的启明星熠熠地闪着。
父亲还是把手收了回来,头颅垂下。边杰又等了两秒,快步上楼。
当晚,边杰做了一个梦。他在一片虚无里面悬着,无边无际。看不见来路,望不见归途。
农村的天气总是偏冷些。边杰立在门旁,这样想着。
今天是除夕,按照村里习俗,在上午需要祭拜一下祖先。
父亲在大门口点燃一把黄纸,再在第一把黄纸上铺开三四把黄纸。底下的黄纸火焰被压下去,只有浓烟从里面出来。还没完全烧完的黄纸,被燃烧的热气冲起来,飘飘摇摇,落进大厅,落到院子里,落到院墙外的柏油马路上。
父亲抽出6支香,在黄纸堆的火苗上点着,走进大厅。父亲的父亲和父亲的母亲的牌位,在条案上摆着。父亲各点3支,拜了三拜,就算结束了仪式。
关于这两位老人,边杰没有印象。往年,也只在清明的时候,边杰才会想起他们。每年清明,村里每家每户都会上山扫墓。坟山就在村后头,连着后村的几亩地。每次上山,父亲在前面领路,边杰在后面跟着。两个人在田间走过,扒开杂草丛,钻进细细密密的竹林里面。烧纸、上香、放爆竹,祭拜、下山、种庄稼。这时候的父亲,比平时更少言寡语些。可能父亲想对他们说的话,都种在了庄稼里,在祭祖的时候才会无话可说。
到了中午,边文、边武驱车赶到,带着大嫂、二嫂,还有边文的儿子边铭和边武的女儿边筱。小一辈的名字总是更愿意找一些生僻字,至于他们是不是更难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则不在起名的考虑范围内。
哥哥们、嫂子们打过招呼后,就去收拾屋子了。边杰帮着他们带孩子,领边铭和边筱出门看看。
“小铭和小筱都读几年级了呀?”
“叔叔,我上三年级啦,小筱读二年级呢!”边铭不怕生,用普通话,脆脆地回答。
“我明年就上三年级了!”边筱带着不服气的语气说。
农村,是方言的自留地。在城市长大的孩子,自然也就不会说几句家乡话。
“那都是大孩子了呢。叔叔带你们去石桥那边玩怎么样?”
“好啊!好啊!谢谢叔叔。”边铭就拉着边杰出发了。
边杰愣了一下。“谢谢”,真是熟悉又陌生的词。
石桥本地话里没有“谢谢”,只有“难为”。村里面乡里乡亲,谁有困难都会捎带手帮衬点。也只有遇上过不去的坎的时候,才会上门求人。被求的人抹不开面子,一般也都会能帮一点是一点。求人的人会千恩万谢,一句又一句地重复着“真是难为你了”,以示对方的大度和自己的歉意。
在边杰印象中,父亲鲜少说“难为”这个词。就算有一年村里发大水,淹了家里好几亩地,一家人也是紧巴着熬了过去。唯一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边杰高一时体检查出了肺结核。父亲知道消息后,一晚上没说话,第二天带着边杰,拎着东西就去村主任家里了。后来,在村主任的介绍下,边杰看了当地最好的医生,病也就慢慢好了。边杰也在父亲的低声下气中,懂得了“难为”这个词的重量。
石桥是很早就有的,村子也因石桥而得名。然而自从修好了大路,渐渐没那么多人走石桥了。不过,要下田地,还是要走石桥。
村里的田,都在石桥那头。
到了石桥,边杰就在桥边蹲着,看着边铭和边筱在田里面撒欢。没下过田的孩子,对田野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两个小孩在田地里,东踩踩西拔拔,享受着没有父母管束的时光。
边杰就在桥边看着他们玩,待到石桥下的小河被远远的太阳烘成暖暖的橘黄色,就喊着他们赶紧回屋了。
除夕晚上的菜,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碗又一碗、一碟又一碟的菜往桌上端。红烧肉、清蒸鱼、白切鸡、松花鸭、烤羊腿……边铭和边筱没感觉这顿饭有什么特殊,吃了几口,就钻进一楼卧室看电视去了。
饭桌上,边文、边武和父亲热络地聊着。从亲戚往来讲到国家大事,从谁家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说到谁家老人今年又去世了。边杰插不进话,也不想聊,吃了两口饭,也就借着帮忙照顾孩子的由头,进了卧室。
卧室里,两个孩子捧着碗,在看动画片。边杰坐在凳子上,心不在焉地看着动画片,过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最后还是坐了下来,耷拉着脑袋,像是一只泄气的皮球,又像是一个放弃抵抗的犯人。
大厅里吃到尾声了,父亲打头,边文、边武跟着进到卧室。边杰浑身紧绷了起来。
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一沓钞票,带着皱痕。他解开绑着的皮筋,从里面抽出3张来。
“小铭、小筱,来拿压岁钱了。”父亲操着家乡话,摇着两张红色钞票说。
“谢谢爷爷,爷爷新年快乐!”边筱抢声喊着。
“谢谢爷爷,祝爷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边铭慢一些,也多说了一段。
他把钱放到两个孩子手上,一人一张,两个孩子再谢了一遍,举着钞票向各自的母亲炫耀去了。
父亲转向边杰,又看了其他两个儿子一眼。从那一沓钞票里面又抽出两张,一共3张放在边杰手里。边杰看了父亲一眼,又低头转向地面,把钱抓在手心,把手垂在脚边。
父亲等了一会儿,见边文、边武没有动作,长叹了口气,转过身。
边文、边武掏出钱包,拿出刚从银行取出的新钞,各自数了一沓给父亲。
“爸,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完成了仪式,没有多余的寒暄,他们也就出了房门。
边杰松了一口气,把钱放进口袋。快步上楼,回到房间。
路灯渐次关了,一楼还在播着春晚。边杰躺在床上,没有睡觉。
不同于手机里面的转账,那3张红色的钞票,那么分明地放在他的手上,像是某种未成年的证明。边杰接下它们,带着某种屈从的意味。
“阿杰。”父亲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边杰直起上身,看着门口。
父亲走进来,从口袋拿出一沓钞票,放在边杰的床上。
崭新的红色钞票,在吊灯的映射下闪着光,散发出一股油墨味。
边杰看着床上的钞票,又看向父亲。
他张着嘴。
他不说话。
窗外,烟花声响起。
新的一年到了。
余修杰(27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硕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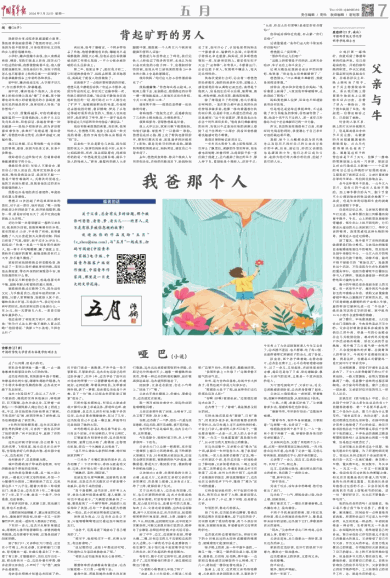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