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自作主张给自己谋了份“田园观察员”的职位。那年暑假,稻禾的清香灌满了整片田野,大地青黄,天蓝得快拧出水来。刚放暑假的我,宛然一条挣脱了罗网的鱼儿,在田野间满怀激情地游来游去,去追捕呱呱叫的田蛙;去寻觅藏匿在稻田里的鸟窝;去用稻草织起稻草人驱赶鸟类……
从露珠打湿衣裳到烟囱吐出炊烟,我玩得忘乎所以。
父母忙着劳作时,我就光着脚跑到河边用塑料瓶盛满水,再跑到200米外的花生地,把水注进住着蟋蟀的筷子般大的小土洞,等蟋蟀吞饱水后,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探出脑袋来等我去抓。我捏着它的两条触须,把它关进透明的小瓶子里,拧上瓶盖。到了晚上,我就听着它窸窸窣窣的啼声入眠,仿佛是在欣赏一曲夏天的赞歌。
我喜欢听蟋蟀那奔流不息的鸣叫,似乎它永远都有唱不尽的动人曲子,在白昼和黑夜嘹亮高歌,能把夏天叫得生机勃勃。
父母的那片稻田种在沙洲地上,旁边挨着一条河,叫清水河。清水河的水位只有膝盖那么深。灌蟋蟀灌到头皮滚落汗水后,我就和伙伴们一头扎进清水河,恍若鸭子一样在河里“嘎嘎”乱叫。大人们见了也习以为常,他们在沙洲地上戴着草帽躬着腰一刻不歇地抢割稻谷,手中的镰刀在空中来回飞舞,骄阳刺过来,瞬间迸发出金色的光芒,连同沁出的汗珠,也那么熠熠生辉。
大人很放心我们在河里戏水。我和伙伴们脱去上衣甩到一旁的大石头上,然后扎进水里,把河水搅得浑浊不堪。我和伙伴们开始比谁在水里憋气的时间更久,输了的人就要表演“小狗过河”。只见那输了的人极不情愿地蹲下,大半个身子泡在水里,只露出头部向前方仰着,双手不停地在水里摆动,踉跄地游向河对岸。看戏者笑得合不拢嘴,到了开学在学校传开后,那便是颜面扫地的事了。
说来丢脸,那扮演“小狗过河”的人就是我。
然后是打水仗。我们分成两队,分别站在河的两岸,一起吼“三、二、一”后,大家将脖子扭向一侧,侧着脸,开始奋不顾身地朝“敌人”泼水。有时一个“敌人”会遭我们全队人围攻,那“敌人”只能边泼边撤,连眼睛都睁不开,嘴里还得咽下几口河水才能缓过气来。有些伙伴还把家里的水瓢偷出来猛泼,最后整条溪河恍如断流了一样,水位硬生生矮下去了一截。那水花一直在空中飞跃,最后又洒到我们身上、碎在河面上。笑声回荡在沙洲地上空,宛如一曲弹不尽的鼓词让人越泼越振奋。
直到河水黄得像泥浆一样,大家才停下战斗,坐在大石头上大口喘气,一起用手擦拭脸上的水珠,然后喜滋滋地啃起甜度不够的甘蔗用来解渴。
水仗过后,河水又变回原先清澈的模样,这会儿我们才开始正式游泳。伙伴们把家里的泡沫塑料拎过来,有条件的便用打满气的汽车轮胎充当游泳圈,我们躺在“游泳圈”上展开四肢,面朝蓝天,慵懒地沐浴着阳光,让“游泳圈”顺着水流缓缓流向下游的开阔地带。
就这样流啊流啊,平缓的流水声缠绵悦耳。霎时,一阵清凉的夏风拂过我的脸颊,像是小时候睡觉时妈妈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令人真想美美地睡上一觉。
再后来睁眼一瞅,青天恍若一汪深邃的大海,几朵轻飘飘的白云点缀其间。倘若有飞机划过,我们定会停下漂流,立起身对着苍穹大喊:“看!飞机!大飞机!”那时,我们在底下蹦跳着向飞机大摇双手,真希望,飞机也能把我们载向山外的世界。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漂流到了村西边的那座木桥旁,这是村里妇女早晨捣洗衣服的宝地。流至木桥,我们的漂流就进入了尾声。
10年后的盛夏,我重返那块沙洲地,蟋蟀还在撕咬夏天,清水河依旧清澈如鉴。又是一年稻谷飘香,大地镶满黄金,河水淙淙,映射着斑斓的波光。我仿佛看见那个载着童年的“游泳圈”从大石头顺流而下,穿过木桥,穿过岁月,浩浩荡荡地漂向了山外的世界。这一次,它再也没有回来过……
欧昌德(20岁) 百色学院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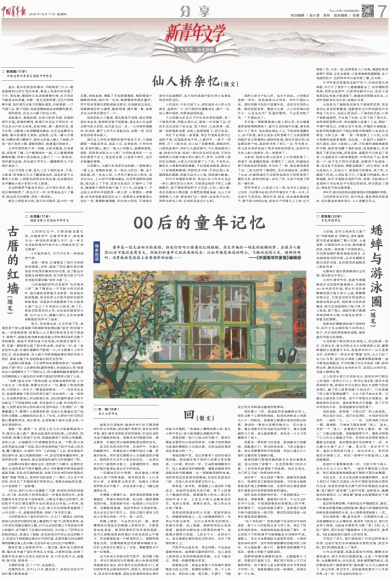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