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切
1984年,林同奇先生去国。林先生将其20多年的思考成果结集出版,起名《人文寻求录》。“人文”何以“寻求”?林先生还在寻求,说明他并未死心,还怀着渺渺一丝希望,碧落黄泉,上下求索,所以读林先生的文字,你能听得见他小心翼翼、开山凿石的敲击声,常常令人心颤。
从“自序”中我们了解到,林先生对人文的神游冥想,始于更年轻的、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他的经历,很像何兆武先生《上学记》里的故事,可能是一代学思者人文寻觅之旅的范本。他先读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中央大学化工系,中途转学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读历史,亦不能满足他对思想、哲学的兴趣。他的幸运,是有一位当时叱奼思想界风云的哥哥林同济,“战国策派”的首领。在林同济的引领下,他读了大量英文原著,奠定了思想漫游的工具基础。他51岁赴哈佛大学,能够迅速进入阅读、交流和冥想状态,皆与40多年前的阅读、思考历程关系重大。相比更多人的绝望,林同奇先生最后还算幸运。可一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少年立志,此后半个多世纪不改,我们就一定能看到作品集中篇篇神思隽永的文字么?人文何以寻求,也不是没有根源的啊。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林同奇先生开辟了自己追回“错失”的独特方法。在我看来,这“方法”中,有思想家史华慈的清晰影响,便是“大问题意识”和对有关人的一切的“关切”。一个人文主义者,最怕丧失掉心灵的内外关照能力和激情。林先生以少有很肯定的语气说,共同的寻求,“是对人(特别是个体的人)的独立存在的寻求,包括对人的内在价值、尊严、自主自立和权利的寻求,”“是对人所具有的特点或结构的寻求,即在人发现自己的独立存在之后,进而力求探索这个存在究竟是什么,”“是对充分实现人的内在价值的寻求,”以期实现“人终必回归到文化的怀抱”之目标。与其说这是林先生的结论,不如说是他的期许。
一代人心曲
梁云平梁某,《树上的日子:我的1968》的作者,1968那一年,17岁。那一年,欧洲的法国爆发了差一点天翻地覆的“五月风暴”,不到一年前,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难,法国五月风暴当口(1968年6月),他的《玻利维亚日记》出版,同年8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祖国大江南北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作者正是围绕这一年,展开了那一代人荒唐史的叙述。
作品重心在第二部,“海南岛岁月”,没有第一部“广州的日子”那么平实。这“岁月”“日子”之差,恰道出梁某一辈人隐秘的心曲,日子,是平和才能过的,而岁月,藏着翻江倒海,生离死别,引颈长歌。作者说道,“说我们是知识青年,可是我们才读了八年的书,初中都没毕业,”“在真正的知识分子眼里,我们却实在连混混也算不上,可是我们却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对象。”梁某接着说,“知识分子的桂冠不是好戴的,是最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必须让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干最脏最累最苦的体力劳动,要我们到广阔天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以便我们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而也就是整两年前,这些“知识青年”在北京接受的还是“伟大导师”的接见,那时的“知识青年”,是学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呢。
结果是什么呢。战天斗地,毁林造田,一把火烧掉百千年的原始森林,到头来弃如蔽履,永难恢复;深入黎族村寨,搅扰其风俗,改造其生活方式,到头来还是拍屁股走人,水已不是那方水,人亦非那方人。要者,当梁某一代人告别山乡,等待他们的城市还是行前那个城市么。
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热情,一代人的生命总能够换回点什么吧。
刘苏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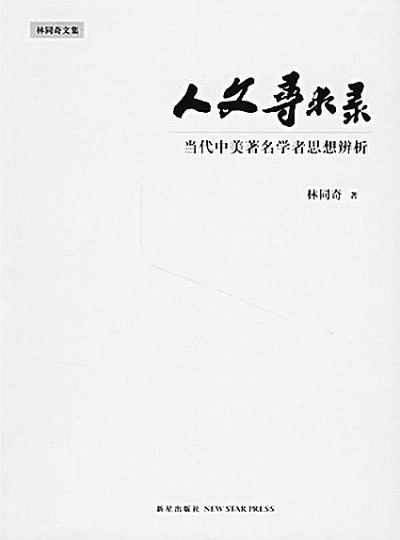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