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和朋友讨论喜欢的著名文人,大概近现代的都没有几个。能逼着我把他著作找完看完的大陆作家,鲁迅算一个,沈从文算一个,胡适算一个……其他的,尤其还活着的,不好定论等着盖棺。我对文人喜欢得少,并不代表讨厌,只是各自胃口不同。或许偶尔看了一篇某著名文人写得比较破烂的文章,便降低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
阎连科便是如此,十年前曾读过他一些短篇小说,觉得土里土气,对于我这个生长在农村向往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生怕会加重自己身上的农民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错过了他的作品,包括《坚硬如水》、《最后一名女知青》等。直到有一天,朋友传给我一份电子书《为人民服务》,我匆匆一瞥,深深为其中的激情和愤怒所震撼。再一看作者,竟是阎连科,当时就想叫一句“好久不见”。
于是,我开始接二连三地找他的《受活》,还有总被人称道的散文《我与父辈》、小说《风雅颂》,才发现此时的阎连科更具备写作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离农村身在城市感受双面生活的我,开始回忆和反思,曾经对农村的无比厌恶变成眷恋,对城市的无比羡慕变成逃离,而喜欢的文字,也随着时间的变迁在改变。
阎连科的文学随笔《发现小说》今年出版,从书中我才知道,他的新小说《四书》未能在大陆出版。接受采访时,阎连科曾说“我觉得写作是与读者在战斗”,在《发现小说》中,他又说“而我——这时候是写作的皇帝,而非笔墨的奴隶”。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挺有道理,畅销书作家把自己的王国拱手让给读者;而经典作家往往将自己的王国蔓延到所有读者的脑海。
所以,单就阎连科书中所谈的大部分作家的作品来说,他们都战胜了读者,成为读者心中的皇帝。譬如他开篇谈到的《鲁宾逊漂流记》,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小说,也算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在《控构真实》一文中,阎连科和奥兹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合约,作家和作者签订的合约,不过前者说的是人物,后者说的是开篇情节和场景。无论人物、事件或者时间,都是合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篇真正完美的小说,合约内容必定是严谨得毫不透风。《发现小说》的第一章,多讲述现实主义风格的历史脉络,这里也涉及同样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家阎连科的影响脉络,他所讲述的真实的四种方式——控构真实、世相真实、生命真实和灵魂真实,构成了他自己写作的维度。而书中,也道出了他在现实主义写作道路上的感叹:“停滞源于控构与人格,源于权力之下积淀的自审心理,源于世相写作的稳妥与经典。”为什么至今我们再难以见到现实主义写作的经典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与作家的自我阉割和自我放弃有关。
《发现小说》全书有三分之二篇章在谈论“因果”,这个词来自佛家,因缘和果报,当然在小说中主要是指原因和结果以及相互关系。这本书里提到的“全因果”、“零因果”、“半因果”、“内因果”等词,无疑是新鲜的。这让我们理解卡夫卡、卡佛、马尔克斯等作家的作品时,又有了新的发现方式。原来卡夫卡的小说并非那么难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绝非全然魔幻。
“故事都是由因和果串联起来的。即使你已经想好一个很棒的结尾,但在故事中生怕立不住脚,所以还得做各种各样的伏笔和填补。这是为什么?皆缘于因果。”阎连科说。现实中不会发生的事情在小说中存在,并非代表小说全然无序,也许某个情节,它是充满因果的,如此一来,合理元素才会逐渐替代想象。所以,阎连科认为,作家头脑中的荒诞情节和荒诞现实,通过因果联系,可以变成小说中可信甚至让人深信的内容。
这与一向写作现实主义作品的阎连科绝然不同,他说自己是“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从另一方面讲,其实也是他的一种突破。于是在《发现小说》的尾章,阎连科提出了“神实主义”——“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或许这样的作品下有着荒谬的一面,但荒谬背后有着精神的真实,内在的因果。它源于现实,却又不同于现实,但最后是对现实的映照甚至比现实更加现实。通过神实主义构造了新的现实,成为“对人和社会敢于真正叩问和怀疑的作品”。在这一章中,阎连科谈到了余华的《兄弟》、莫言的《酒国》以及其他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某些突兀的情节,往往令人记忆犹新,而这些突兀,都因为与现实不符却在小说中成为合乎因果的亮点。
我并非文学理论家,对阎连科所提及和创造的一些专有名词依然一知半解。更多的时候,我在试图发现《发现小说》中所提及的小说和小说家写作的秘密,那些故事背后的密码,那些不真实情节背后的真实存在,往往让人感叹当下多数小说的堕落。太多的作品停留在对现实世界的美好感知和想象中,于是现实的残酷一面被遮蔽。这些作品停留在自我的意淫中,而忽略了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所以,不少作家沦为了笔墨的奴隶,虽然在他们内心还穿着皇帝的新衣。
黑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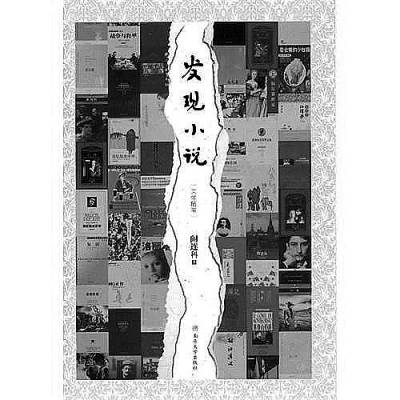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