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1977.11-2013.3)杰出青年学者,上海崇明人。
在学者张晖埋首古籍、读书写作的间隙,他常常会望见窗外那座十三层的八角形砖塔。那是明代万历四年兴建的塔。昔时,砖塔檐角下挂着3000多枚风铃,微风拂过,清脆之声遍及四方人家。但当张晖从住所望去,风铃早已不见踪影。
在新书《无声无光集》的序言中,36岁的张晖提到了这座“无声无光”的石塔,并感谢书中有声有光的人文世界,伴他度过无声无光的日日夜夜。
这是他一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他甚至没来得及将成书赠送给师友。2013年3月15日,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这位青年学者在北京逝世,留下了妻儿、年迈的双亲,未还清的房贷,还有不知其数的资料与文稿。
张晖是中国社科院年轻的副研究员,但他已出版过《龙榆生先生年谱》、《中国“诗史”传统》、《清词的传承与开拓》等5本专著,还有着已经排列到2015年的工作计划。他曾在南京大学读了7年的文史,之后又在香港科技大学与台湾中研院做博士与博士后研究,因此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少见地有着贯通西学的眼光”。而他又极为用功,在去世前半个月的某天,他数了数自己手头,竟同时进行着8项工作。
“他的眼光比同龄人开阔。”张晖在社科院的同事王达敏这样形容他,“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张晖长得颇为敦实,方脸浓眉,金属边的眼镜朴实地架在鼻梁上。年轻时他很瘦,有同学觉得看着像香港演员陈豪。平日里,他低调寡言,礼貌谦逊,被文学所里的年轻女同事形容为她们的理想结婚对象。
但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一个喜欢畅谈文史、理想与抱负的人。聊到兴起时,他神采飞扬,能滔滔不绝地说到凌晨四五点。
张晖的高中好友维舟相信,在沉稳的外表下,他有着“犹如岩浆一般藏于内心的深情”。维舟还记得高考前,班上女同学说,选历史是因为考试容易,张晖听了,连连摇头,那时他已经极爱文史。
不止一个人说,如果老天再给十年,张晖原本可以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最优秀的学者之一。
在同学的记忆中,沉静的张晖也会流露孩童般的天然痴气。他爱喝可乐,爱吃美食,跟孩子玩得好。在中学里生病,他会在托同学带饭的单子上指名要杏仁和话梅;在香港读博时,满记甜品和西贡的海鲜大餐让他感叹“好吃得快要哭了”。
直到在医院见到了张晖的父母,蒋寅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位气质文雅的同事,来自一个地道的农村家庭。张晖成长于上海的崇明岛,在高考之前,父亲对他说:“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但老人家最终还是被儿子说服了:在冷门上做出成就,比在热门上庸碌无为要好。
后来,张晖曾对维舟提及,在香港最令他感动的一点是,在那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很多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
说起来,自高一那年的春天起,文史就成了张晖的挚爱。在崇明岛的十八里乡下,语文老师将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误讲成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但即便如此,张晖还是贪婪地阅读所有他能找到的文学典籍。他开始研读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篇》,被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所打动,并寻找各种红学著作。此外,还与同学维舟一起搜罗各种诗词书,一字字复原平仄,试着填词作诗。为了读书,他们翻遍了县图书馆与学校的图书室。
对图书的热爱与搜寻后来成为一种习惯,贯穿了张晖的学术生涯。将他引进社科院的蒋寅对这位后辈搜集资料的能力印象甚深,形容他“到哪儿都留意,哪里有图书”。另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学界的前辈都认识张晖,他与很多老辈文化人的后代都保持着联系。
去世前,张晖还在写他计划中“南明三部曲”的第一部《帝国的流亡》。书中主要描述了在南明小朝廷中,面对天崩地裂的转变,大量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坚守与挣扎——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下,文人如何坚持信仰、实践理想:有人自杀殉国,有人投降,也有人陷于绝望,遁入禅门,或是成为满清土地上的前朝遗民。他常常一写就连着几个通宵。
直到去世,张晖也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3月14日早上,他起床后觉得“浑身疼”,到了下午突然昏迷,晚上6点多被送到医院后,他还是自己走进去的,不久之后就瘫软了下去,妻子呼唤他的名字,而张晖只是虚弱地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友维舟曾问张晖:“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但张晖回答他:“冷板凳总要有人去坐。”
“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他说。
在张晖弥留之际,蒋寅甚至一度后悔起了将他引领进社科院,令他带着总也升不高的薪资与职称在北京城中辛苦地谋生。早在张晖在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听说过这个年轻学子的姓名。“他属于特别少年有成的那种人,在本科时代就能出书,是极其罕见的,吴小如先生说过,博士生论文也未必能达到那样的水平”。
曾几何时,博士毕业后的张晖来京求职,手中握着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聘用书,而蒋寅力劝张晖到工资微薄的社科院文学所工作。那时蒋寅相信,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在这里做学问,对这位自小以学术为志向的学人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说到这里他声音突然一低:“只是我也没有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
有一次,语言学家张振兴也惊诧于文学所的清苦,老先生当时问张晖:“你也可以写小说补贴收入嘛,写小说谁不会?”
结果张晖笑了起来,说:“我就是不会。”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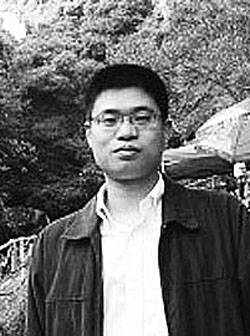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