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开饭了,望着餐桌上精致的食物,12位美国小伙的心情却十分复杂。尽管这些食物都免费供应,厨师也长期为德国的名媛掌勺。
对这些收入微薄的年轻人来说,这餐饭既能给他们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还能享受一把上流阶层的待遇,但这种待遇不能白白消受。这12个美国小伙是一项科学实验的志愿者,《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给他们起了个更响亮的名号:试毒队。在美国农业部化学物质司的专用餐厅里,“试毒队”成员们一日三餐都要吃下含有化学添加剂的食物,测试这些可疑物质对身体的影响。
严格来说,食品添加剂并非全部有毒。可就像“试毒队”这个名号一样,在媒体这个放大镜下,人们的情绪成倍放大。这项“以身试毒”的实验成了美国人集体恐慌的一个缩影。
食物让人害怕,这听起来不合逻辑的说法其实细想之下也不无道理。至少在美国麦克马斯特大学荣休教授哈维·列文斯坦看来,对食物的焦虑已经成了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特征。他把这些焦虑记录在他最新的著作里,名字就叫《让我们害怕的食物》。
渴望又恐惧,如果将时间轴拉长,人们对食物的这种复杂情感也许是远古的遗传。
在人类还只能通过狩猎和采摘果腹的时候,食物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哪个果子有毒,哪个果子没毒,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到了今天,人们对食物的焦虑不再源自神秘的自然,而是更加复杂的人性。摆在你餐桌上的牛奶,牧场在澳洲的某一片草地,加工和包装也许到了亚洲某个小镇的工厂,而它的检测标准可能又来自欧洲。
人们对食物新的焦虑,给“试毒队”的举动渲染上了一层悲壮的英雄色彩。马戏团里甚至都传唱起了歌颂“试毒队”的曲子:“他们每顿饭都要吃一批毒药。早餐是加了氰化物的肝脏,切成棺材形状。”
虽说“试毒队”的成员都签下了生死状,但谁都不希望他们真的牺牲。这场轰动性的冒险是发起者获取公众支持的手段,最终目的是一部全国性的纯净食物与药物法案。
他们也确实成功了,这些年轻人一日三餐吞下“毒药”的画面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几个月里促成了过去23年都没能颁布的法案。
听起来像是一个励志故事的圆满结局:正义的一方用勇气和智慧战胜了邪恶,从此世界和平,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法案颁布之后,关于有毒添加剂的故事依然定期横扫全国,反复唤起人们对食物的恐慌。归根结底,制定、执行法律的,依然是纠缠在利益中的人。
那些被认为利用有毒添加剂牟利的大公司,不仅没有反对法案的颁布和执行,恰恰是法案的积极推动者。对他们来说,严格的检查措施帮助他们扫清了与之竞争的小公司,还给自己盖上了“权威认证,安全健康”的印戳。至于原来那些小伎俩,只要“与时俱进”就好。
当然,“德先生”搞不定食品问题,“赛先生”也没法打包票。梅契尼可夫,这位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发明了一种“自体中毒理论”。比起食品添加剂,这位大科学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食物本身。他认为,人体巨大的肠道是“史前时代的遗迹”,在当下,烹饪已经取代了肠道原有的消化功能。“多余的肠道”会让食物堆积、腐烂,成为“有毒微生物的庇护所”。
给全世界下了一纸“你们都有病”的诊断书,这位大科学家还没闲着,转身又开过来一单药方。“酸奶!酸奶可以杀死这些有毒细菌!”“认准梅契尼可夫授权的酸奶药丸!”还有更多跟风的企业凑上来,“我们也会做‘科学发酵酸奶’,喝了我们的,就能活到两百岁!”
梅契尼可夫自己还是保守一些,把酸奶的效用“缩减”到140岁,不过,随着这位科学家在71岁因心脏衰竭离世,这股酸奶热潮也暂时消退了。
在现代社会,人类对食物膨胀的欲望,催生了庞大的生产系统。食物的生产、加工以及处理正在从家庭走出,嵌入到不断膨胀的全球体系之中。在摆上餐桌以前,食材已经走过了无数陌生人的手,也为在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创造了牟利的机会。
对安全食品的期待,当然不能仅仅指望所有人都有道德自觉。人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法律、制度或者权威专家,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些都不是万全之策。就像列文斯坦在书中说的那样,如果说以往的焦虑来自食物,那么人们当下对食物的恐惧,则是源于利益纠葛的人类本身。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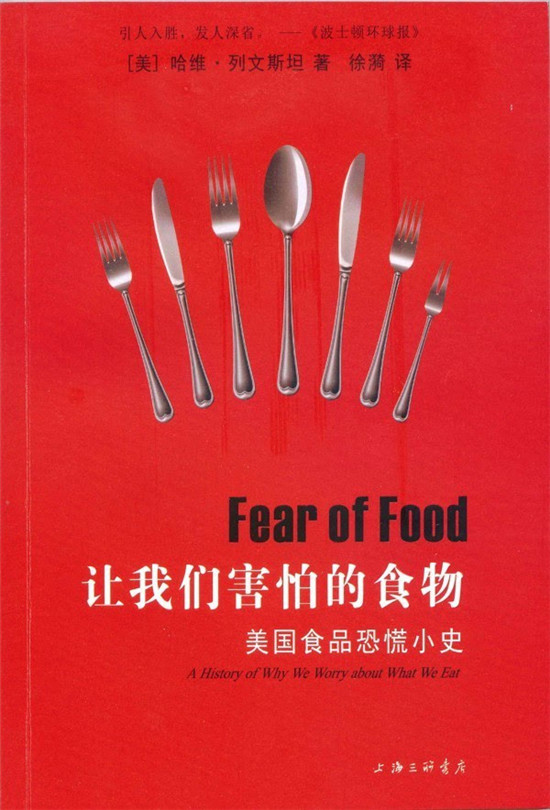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